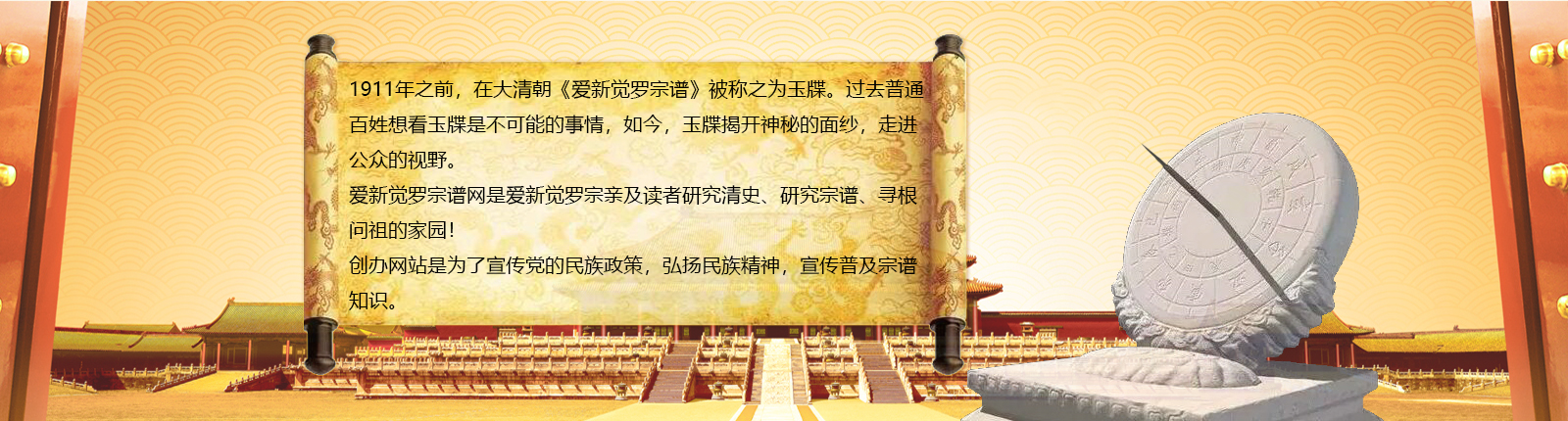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岁月往事】/回忆族亲
爱新觉罗·溥仪先生
作者/爱新觉罗·启泰
我的族亲、尊敬的长者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去世已经整整26年了。虽然,他生前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他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乃至音容笑貌都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对社会主义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也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爱新觉罗·溥仪是我的远房族亲,按照清朝道光七年续拟的《爱新觉罗宗谱》中“溥、毓、恒、启”四个字辈,溥仪先生和我的曾祖父溥荫同辈,长我三辈。1960年1月,在溥仪的七叔载涛家里听载涛先生说:“咱们的大爷(北京满族对排行老大的称呼)回来啦,在崇文门旅馆住着呢,你有时间可以看看他去。”当时我只是从报纸和广播中知道伪满洲国皇帝、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被特赦释放的消息,这次有机会见见这位被共产党改造好的封建皇帝,是求之不得的。我按照载涛先生的指点,乘公共汽车来到溥仪住地。热心的服务员将我领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轻轻叩开了门。只见一位身材硕长、戴着黄边眼镜的老人用十分地道的北京话问我:“您找谁?”我愣住了,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怎么看也不像个皇帝呀!他听服务员介绍是找他的,于是便很客气地做了一个手势,说:“请屋里坐。”我进了屋,说明是涛七爷让我来的。溥仪先生按照满族习惯给我沏了一杯茶,送到我的手里。当他听说我叫启泰时,竟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噢!你是‘启’字辈的,前些日子我见到启功了,他是咱们家族里最有出息的人,现在当了大学教授啦!咱们都得向他学习。”我问溥仪先生住在这里方便吗?老人指着床上放着的一件新棉大衣说:“这是政府新发的棉大衣,在这儿住着吃饭,洗澡都挺方便。出门往北走不远儿就是东单,坐公共汽车上哪儿都挺方便。政府每月还给60块钱的生活费。”溥仪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谈话很随便,我并没有因为他过去当过皇帝而感到恐惧,他也没有因为我是晚辈而以长辈自居。我不禁想起了父亲在1934年随北京的宗室觉罗们(清朝皇帝的远近支亲属)去东北长春参加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时的情景。当时,溥仪端坐在宝座上,威风凛凛地接受宗室觉罗们向他行三跪九叩礼。父亲每次提起这件事就说:“磕了半天头,连‘皇上’长得什么样都没看清。”时代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溥仪先生很关心我的家庭情况,问这问那,我一一做了回答。看来他很满意,接着溥仪先生向我介绍了他回北京后的一些情况。回到北京的第5天,敬爱的周总理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溥仪和其他特赦人员。他说,见到总理我非常激动,当时只是紧紧地握住总理的手叫了声:“周总理。”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周总理在讲话中提到了满族,他说,在解放前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有的人更名改姓。这是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产物。解放以后,新中国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满族不再受歧视,在第二次填报族籍时,很多人自报了满族。总理还风趣地说:“满族妇女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一看就知道是满族。现在有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就没有必要用生理特征辨别民族了。”总理说完哈哈一笑。溥仪先生对我说,听了总理的讲话,联想自己所看到的事实,非常受感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满族人民才真正得到解放,爱新觉罗家族才有了兴旺发达的今天。我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民族,又怎能不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呢?溥仪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说,这些日子政府还为我们这些人安排了一些参观活动。我们先后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人民公社和清华大学等十几个单位。在人民大会堂,溥仪先生听说这里能容纳万人开大会,宴会厅能同时供5千人就餐,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之多,比他当年居住的紫禁城皇宫还大得多。而从设计施工直到工程全部竣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面对这一伟大的工程,他又一次感到了人民的伟大,共产党的伟大。在民族文化宫参观时,溥仪先生兴致勃勃地登上了13层的主楼极目远眺北京城。此时,做为少数民族的一员,他的心情更加激动,他说:“几千年的历史上都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清初,满族皇帝统治了中国,又对其他民族压迫、歧视。到了中华民国,虽说是‘五族共和’,但少数民族仍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解放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尊重。少数民族像程砚秋、老舍等这样人的才能才得到了发挥。”说到这里,溥仪先生又提起了他的四弟溥任,为筹建民族文化宫,溥任先生捐献了一批自己家里珍藏的古籍,以此做为少数民族对筹建民族文化宫的一点心意。溥仪先生对四弟的这个举动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四弟捐献的不仅仅是几十本书,而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片心,是少数民族的一片心。”溥仪先生谈兴正浓,我也听得几乎入了神。服务员来通知他开饭了。我歉意地起身告辞,溥仪先生想留我共进晚餐,我婉言谢绝了。他有礼貌地送我到旅馆门口,一再嘱咐我回到家里代他向我的父母问好,并说以后可以和他通信。在寒风中老人站在旅馆门口向我挥手告别,目送我朝着公共汽车站走去。
我第二次见到溥仪先生是在1963年底。这时,溥仪先生早已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并列席了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和常委(扩大)会议。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已和李淑贤女士重新组合了家庭。我在全国政协机关接待室见到他时,正值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前夕。溥仪先生显得异常忙碌,清癯的脸显得更加消瘦,但看上去还是很精神。据溥仪先生自己介绍,这本书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前后共用了6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先后五易其稿,现已基本定稿。原来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悔过自新。另一方面,是让读者从自己的切身体验的新旧社会对比里得到公正的结论。溥仪先生又说,修改这部书稿,周总理很关心,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方向性的建议。周总理说,这本书是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你就站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个皇帝让共产党给改造好了,能交待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待。总理还要求,修改这本书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认真核实每一条资料,做到准确无误,更要有战斗精神。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溥仪先生和帮助他写作的李文达先生又经历了许多周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此同时,在搜集资料方面也得到了当时尚在世的、原在清宫待过的老先生们的支持。在修改定稿过程中,又得到郭沫若、翦伯赞、翁独健、老舍等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的热情帮助。最后形成了一部42万字的成书。溥仪先生说,这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功劳应属于大家。这次和溥仪先生见面,我看老人家实在太忙了,不忍心再继续打扰,便匆匆告辞。临别时,溥仪诚恳地对我说:“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一定送你一本。”我当即表示感谢。次年5月,我果然收到了溥仪先生给我寄来的一本《我的前半生》。书的封面为灰色,印有作者自己题写的书名,并有一小型的作者印章。书的扉页上作者用钢笔写上了“启泰宗彦雅正。溥仪”八个苍劲有力的字。我见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一口气通读了一遍。读后,确实受益匪浅。可惜,这样一本曾经被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肯定的好书,在“文革”中竟被污蔑为大毒草。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我有这本书,无法隐瞒,只好忍痛割爱将这本书交给了造反派头头,至今下落不明。
《我的前半生》出版发行以后,很快轰动了全世界。人们争先恐后想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封建皇帝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中国公民的伟大奇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87年,国内中文版总印量达170万册以上。外文出版社也先后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德文、阿拉伯文、印地文、乌尔都文……出版发行。许多国家也先后将这本书译成本国文字向本国读者推荐。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溥仪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党的伟大改造政策,使我得到了光荣的新生,使我分清了是非,认识了真理。真理越接近我,我就越仇恨自己的过去,新生溥仪是坚决反对皇帝溥仪的。我已用文字写下了一本书——《我的前半生》。今后,我将用实际行动写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不断学习和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与祖国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由此看来,溥仪已经由一个封建皇帝、战争罪犯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民,并且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着自己的后半生。
万万没有想到,溥仪先生由于病魔缠身,在“文革”期间得不到及时治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967年10月19日,当我从广播中听到溥仪先生逝世的噩耗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怎么就突然死了呢?溥仪先生刚刚开始了他热爱的新生活,又匆匆地离去了,他死得确实太早了。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溥仪先生的葬礼十分简单,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政协在北京为溥仪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在溥仪先生的悼词里,党和国家对他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指出他是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民日报》也以显著的版面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消息。会后,在八宝山公墓重新安放了溥仪先生的骨灰,尊敬的老人在九泉之下得到了慰藉。
溥仪临终时说的一段话:“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但我还没给党做什么工作……”在他离世的时候,没有考虑自己的后事,而想到的是“还没给党做什么工作”。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建设四化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抛弃,还有什么舍不得牺牲的东西呢?
(编者注:此文章于1993年发表在《中国民族》杂志第10期上)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