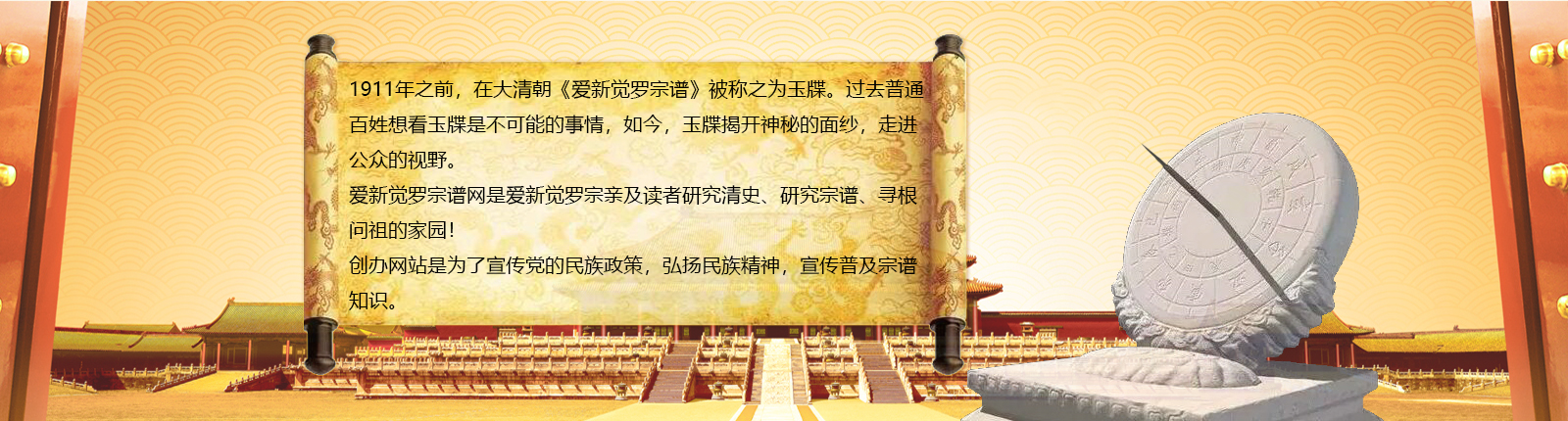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作者:关捷(沈阳作家协会副主席,满族,瓜尔佳氏)
如今,每当我走到宗人府胡同,那个住过高塞的地方,每当走到万泉公园,那个东平书院、东园、淡园所在的大致方位,我都会投去景仰的目光。
尤其是万泉公园,她是清代诗歌起飞的地方,这里曾有种菊人、赏菊人,这里曾有种海棠的人,赏海棠的人,那些赫赫有名的大诗人,那些携带菊香、携带海棠香的诗歌飞满天。沈阳,千百年来与诗歌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沈阳的诗歌历史相当厚重。隋炀帝杨广在这里写过《纪辽东二首》、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写过《辽城望月》、金代王寂在这里写过《沈州吊古》《渡辽舟中小酌》、赵秉文在这里写过《庆云道中》、吕子羽在这里写过《宿章义广胜寺》、明代王之诰在这里写过《渡辽河坐新舫中》、冯惟健在这里写过《沈阳道中》……
但到了清初,具体说是到了顺治初年,诗人们的笔在惶恐中停了下来。即使有人写诗,也都是“地下活动”。

1
直到诗歌史上一个明星式的人物出现。
顺治元年8月20日那天上午,在清王朝迁都的大队人马中有一位少年,少年的目光对故乡沈阳似乎颇为眷恋。他秋月般的小脸上,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人们以为,沈阳在清初的时候只有金戈铁马,并不知道居然还有菊花与海棠,还有诗人与诗歌。
现在,如果忽然有人说沈阳是清诗的发源地之一,会招来反对吗?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实在是对一个伟大诗人及其卓越贡献缺乏足够的了解。
此人是满族的第一位专业诗人,更是清诗的开拓者。
马背上的这位少年就是皇太极的第六子、顺治的六哥爱新觉罗·高塞(1637-1670)。当年顺治迁都北京的时候,他只有8岁,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深情的目光属于诗人的目光。
在《清史稿》里,关于这位公爵只是寥寥几行字—“镇国悫厚公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进镇国公。高塞居盛京,读书医巫闾山,嗜文学,弹琴赋诗,自号敬一主人。九年,卒。”
高塞的五世族孙、清嘉庆年间的礼亲王昭琏(1776-1830)在《啸亭杂录》中描述道—敬一主人,讳高塞,文皇帝之第六子也。封镇国公,世居盛京。主人善文翰,诗多清警。爱医巫闾山幽雅,尝于夏日读书其间,有辽东丹王之风。……”
那么,“辽东丹王之风”是什么风度?
辽代的东丹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辽世宗耶律阮的父亲。公元926年,被封为“东丹王”。他自幼聪敏好学,修得文武全才,不但善于骑射,而且文化修养也很深厚。他有个令世人惊叹的壮举,就是从中原买了万卷书,收藏在他隐居的医巫闾山绝顶之上的望海堂,从此日夜研读。久而久之,耶律倍就通晓了音律,而且精于绘画与医术,工于契丹文和汉文的文章。他是集藏书家、医学家、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汉学家和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
高塞也是皇子,除了在盛京居住,他也喜欢像耶律倍那样住在医巫闾山读书,而且也精于绘画与诗歌。因此,礼亲王昭琏才说他“有辽东丹王之风”。
2
据载,顺治皇帝可以成段地引用金人瑞评点过的《西厢记》……他对金人瑞的评语是“才高而见僻”。可见,他对《西厢记》的精熟程度。而且,成年之后,他本人也兴致勃勃地写起了诗歌。他为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皇太后)而写的《万寿诗》,就写得很有特点。
按照皇家子弟年满6岁即开蒙的规定,高塞的书房里应该配备满文版的“经史子集,稗官小说”……还有满族人特别喜欢的《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
然而,让高塞终于选择文学还不只是《三国演义》,而是比《三国演义》更恐怖的现实。
大哥豪格(1609-1648)在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被削了亲王爵,说得出的理由是语言中伤了睿亲王多尔衮(1612-1650)。可能多尔衮也觉这个罪名太牵强,到了十月,又给恢复了王爵。虽然如此,多尔衮对这个大自己三岁的侄子还是不太放心。
二哥、三哥早亡,不必再说。四哥叶布舒(1627-1690)已经年满16岁,新皇继位本来应该加封的。但10个月过去了,旁支的宗室王子都已加封,作为本支的叶布舒却还是一个普通的皇子。而且,任何战役战斗也不让他参加,这就等于剥夺了他加官晋爵机会。
15岁的五哥硕塞(1629-1655),目前也没有什么封爵迹象,其他兄弟还小,未来不可预测。但从他们母亲的眼神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拉氏的惶恐不安。
大哥豪格的削爵与复爵,是多尔衮向顺治帝其他兄弟的一次威吓。只有顺治的兄弟们温顺了,顺治本人才能安全一些,刚刚崛起的清王朝才能安稳一些。这是多尔衮的思考结果,当然也是孝庄的治国逻辑。
清初的内外局势复杂,好多选择也是无奈的,是铁面孔的。
3
聪慧的六皇子高塞能读懂《三国演义》,他当然也能读懂大清国初年的“宫廷演义”。
宫辇继续前行,顺治元年8月20日中午的时候,故都的宫殿像烟云一样消失了,连高大的凤凰楼也看不见了。高塞依依不舍地收回了他眷恋的目光,但他似乎已经萌生了回乡的念头。
有人说,高塞那天压根儿就没走,直接在盛京开府建衙了。然后,一头扎在这里读书写诗。
但,这个可能性是零。
无论是多尔衮,还是孝庄都不会把一个8岁的皇子丢在盛京。再说,8岁也不到开府建衙的年龄,清礼制规定,皇子年满16岁才可以走出皇宫开府建衙。
在苗君稷的《焦冥集》里,有16首是书写高塞的专题,每一首都尊称他为“辅国公”,而高塞晋封为辅国公是在顺治九年九月。那年,他17岁,敕造的公爷府在北京的板桥胡同。大约此后不久,他才回到盛京另外开府建衙的,才与流落在关东的苗君稷等一大批蒙难的诗人相遇。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高塞执意回盛京久居呢?仅仅是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祯(1634-1711)在《池北偶谈》中说的那样为读书写诗吗?如果是为了这个,在北京或北京周边完全可以做得到呀。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恶化的局势——
迁都到北京第三年的年初,大哥豪格自杀。顺治三年的正月,豪格被授“靖远大将军”,征伐四川。经过11个月的激战,到十二月,彻底剿灭了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班师凯旋。1个月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而被多尔衮构陷削掉王爵,幽禁了起来。到了四月,豪格不甘屈辱,自尽身亡,年仅40岁。朝野一片震惊,同时也是一片沉默。
四哥叶布舒依然不得封爵,五哥硕塞虽在因为母亲叶赫那拉氏的高贵身份而勉强封了亲王,但在豪格事件后,却又降为郡王。不久,他郁郁而终。
高塞对弟弟顺治封他的宗室六等宗室贵族头衔辅国公,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想念盛京。
4
顺治九年封爵之后,高塞可能以“陪护父皇”“陪护祖宗”为由向顺治帝提出回盛京居住。这个时候,多尔衮已去世两年多,朝廷正是用人的时候,而高塞在众皇子中又是才华横溢,如果顺治信任六哥的话,完全可以挽留他。但顺治顺水推舟了。
于是,高塞就毅然踏上返回盛京的路。一个美丽而智慧的女人跟在他身后,那是他的福晋颜扎氏。颜扎氏是一等子爵赉图库的女儿,自愿为皇太极殉葬的将领安达礼的孙女。查《爱新觉罗宗谱》,高塞是极其罕见的没有纳妾的公爵,这似乎可以证明两人之间的感情。
刚一踏上永安桥,高塞就看见盛京总管叶克书(?-1658)率领众官员正笑容可掬地恭候在那里。
那么,高塞的公爷府建在哪里呢?或者说,叶克书将军把他的住房安排在哪里了呢?
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请教过好多人,都说不太清楚。有一天,我问到沈阳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研究员周维新先生,他说:“大体上应该在宗人府胡同里面,就是现在沈河区检察院的位置,上世纪五十代初的时候,那一带有好多精致的大四合院,规格仅次于贝子府。高塞的公爷府应在其中,据说,这片的院子都是入关前公爷们的。他回到沈阳,应该就安排这一地区的某个大院。”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的宗人府胡同
如此说来,辅国公高塞是咱们沈河区的老居民了。正值青春年少的高塞率领最杰出的诗人们吟诗作赋,他们也从这里出发,去拜医巫闾山的观音阁、拜千山莲花峰的龙泉寺、祖越寺、拜永陵、拜福陵、拜昭陵,然后,带着满身的野花香归来,谈笑风生地走回府第……这应该是当年盛京城里一道诗意盎然的风景线。
可惜,高塞的老宅子踪影皆无了。据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居民把那一片的大宅院全部改成了大杂院,再后来,连大杂院也没有了。
但也不要失望,这并不等于说高塞在沈阳就没有其他的遗迹。遗迹还是有的,比如现在的棋盘山向阳寺和万泉公园。特别是万泉公园与他的关系,简直像诗歌般美丽,内容涉及他对知识分子的友好态度,对诗人的亲和态度。
5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他回到故乡都做了什么。
高塞为自己取好了字号,号“敬一主人”“敬一道人”,又号“霓庵”。取这样的字号,一副出世的姿态,他等于给自己穿上了“迷彩服”。
在《池北偶谈》这本书里,王士祯进一步描写道:‘敬一道人,性淡泊如枯禅老,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理。常见仿云林(倪瓒)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虽士大夫无以逾也。’”
三笔两笔,王世桢勾勒出一个陶渊明,清朝初年的陶渊明。
在绘画方面,高塞崇尚元代的倪瓒,追求“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
这就有趣了。
他可是真正的王孙哪,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他本来顺理成章地可以写风花雪月,可以写故都的琼楼玉宇。然而,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意思。
王孙归不归?王孙归,王孙归了田园。
高塞的笔墨选择了另一种背叛,对于王的背叛。他的创作主要是山水诗,山水诗又兼有释道精神。比如《宿向阳寺》——
圣朝存象法,古寺复闻钟。花引山门路,云开野殿松。高斋谈静理,远屿淡秋容。日暮还携杖,月明林外峰。
向阳寺,位于沈阳城北棋盘山北麓,它四面环山,避风向阳,因而得名,是一座始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的古刹,据说高塞的祖父努尔哈赤曾到这个寺庙与老方丈谈论天下大事。

向阳寺
现在高塞也来了,而且还住了几天,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的态度很明确,“花引山门路,云开野殿松。高斋谈静理,远屿淡秋容。”,他要的仅仅是这样的理想国,他是来参佛的,他已经完全没有祖父那样的雄心壮志了。
高塞其他的诗作也大致如此,风格基本上稳定。比如在《秋怀》中,他坦诚写道:“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尊酒,沉酣据玉琴。”一幅活脱脱的自画像,自画了“闲云野鹤”的形象。他的绘画艺术也是同样的恬淡,比如备受画界好评的《琼娥图》,仿佛特别出世的形象。
高塞在移居盛京最初的几年里,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情形
6
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好像是发生了反转。他后来好像还是脱掉了“迷彩服”。我总感觉高塞后来身上另外负有特殊使命,不信就接着往下看。
应该是在顺治亲政之后的某年,他接受了一个特殊使命。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记载,顺治十一年七月末,他回了北京一次,因为当月的二十三日他的母亲那拉氏在慈宁宫去世,顺治帝给予高规格的葬礼。
“是日,上赐祭文纸张羊酒等物,遣官谕祭辅国公高塞之母。内弘文院缮拟祭文,送礼部誊抄于黄纸,于七月二十三日遣侍郎渥赫等捧祭文赴茔所。祭文在前,部员随后,一并至茔所。高塞公跪迎于门外,然后随入,捧祭文入门,陈红毡案上,金银楮币摞于燎位,供案就绪。遣官正中跪,诸官随跪。由礼部员外郎萨木哈立读祭文曰:维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帝钦派礼部侍郎渥赫等。谕祭辅国公高塞母之灵曰,尔为皇考之小福晋,忧勤年久。于内廷谨慎小心,忠勤敦厚,尤为可嘉。正欲安生长寿,不料溘逝,故特颁祭葬,以示怜恤。尔若有知,尚克咅欠享。读毕,遣官跪奠三爵,每奠一叩,诸官随礼。毕,捧祭文置燎位,与禇币一并焚之。”
高塞对此的回应是“望阙谢恩,三跪九叩。”
顺治皇帝对庶母如此礼遇,至今为止,在清代档案里还没有发现第二例。
君臣之间、兄弟之间的感情因此悄悄发生了变化。
7
高塞从北京再回到盛京,竟然公开“礼聘天下贤士”。说是大家要聚在一起研讨并创作诗歌。这如果没有朝廷的允许,一般来说是不大可能的。“礼聘天下贤士”?想干什么?如果没有特殊背景,这样的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头一个来公爵府报名应聘的,是被称为“东南诗人之冠”的常州诗人蒋鑨(1625-?)。这个人曾著有诗集《吴越放言》《闽游草》,编有《清诗初集》。有人说他是被流放盛京地区的,也有人说他是到东北来旅游的,不管怎么样,看起来是不大得志,但高塞也选中了他,给他安排的具体工作是让他编选诗集。
紧接着,来敲公爵家大门的是陈维崧,这个人物的出现证明了高塞真的接受了特殊使命。
陈维崧(162-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末清初的词人,文学界的“江左三凤凰”之一,即清初的三位文学大家,宜兴的陈维崧(1625-1682)、吴江的吴兆骞(1631-1684)、松江的彭师度(1624-?)。陈维崧这人特别喜欢作词,一生写了有一千六百二十九阕之多,古今词家所未有,著有《湖海楼全集》等。这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文学史上“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之一陈贞慧的儿子。问题的奇妙就在这里。
陈贞慧(1604—1656),是明朝末年的左都御史,身上带有明显的反清政治倾向。明亡以后,隐居家乡亳村11年,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直至逝世。那么,他儿子来盛京干什么?
此外,至少还有3名政治危险人物是高塞在盛京结交的密友。他们是函可、苗君稷、孙旸。
函可(1612-1660),是明代最后一个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是清朝开国陷入“文字狱”的第一人。因为写作记录顺治二年战乱的《再变记》获罪,又于顺治五年蒙恩敕住沈阳慈恩寺修行思过。高塞不但没有回避这个人物,反而和他亲密接触,视他为朋友圈中的贵重人物。
苗君稷(1620-?),作为明朝遗民,他甘愿在三元观里做道士了此一生,曾经发誓不与大清合作,连皇太极多次邀请出山,他都婉言谢绝。然而,皇太极的儿子高塞轻轻一招手,他就走出了山门,并很快成为高塞的密友。高塞居然可以和这个道士同居一处数日谈诗论道。在苗君稷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两人在一起“宴饮”“祝寿”“观猎”“游东园”“淡园咏海棠”等场景,足见其亲密的程度。
孙旸(生卒年不详),是因受顺治十四年科场作弊案牵连而流放到铁岭的罪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孙旸流放的10年中,他完全是处在“监外执行”的状态,日子过得又悠闲又优雅。这都是高塞一手为他办理的。孙旸好像就是先到铁岭的监狱尚阳堡报个到,履行个手续之后,就急急地来到了盛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辅国公府里畅谈文学与诗歌。
一个一心想远离政治中心来到陪都隐居的皇子,他怎么可能与朝廷的罪人高调来往呢?
这如果背后一点故事没有,高塞是不可能如此胆大妄为的。从史书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高塞是个特别谨慎的人。
还有个细节,可为我们的猜测提供有力的佐证,这就是一个叫猛峨的郡王爷来到盛京看望高塞,并且写诗与苗君稷等诗人互动。
猛峨(1643-1674),是高塞大哥豪格的第五子,是他的侄子,顺治封的温郡王。从苗君稷的《恭温王殿下十四韵》和《恭温王殿下原韵》诗来看,来盛京的时间应是封王之后,即顺治十四年之后。
那么,这位温王殿下是来干什么的?是来看六叔的吗?是来旅游的吗?清礼制规定,郡王、贝勒等没有朝廷特旨不得出京。现在猛峨不但出了京,还到了六叔的府上,并且特别难以理解的是,堂堂大清的郡王爷居然与有严重问题的苗君稷唱和起来。那么,他得到的是什么内容的圣旨还不清楚一二吗?
8
高塞把这些有问题的人物请到辅国公府里,竟像亲密朋友一样,像贴心知己一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诗论画。渐渐地,竟然形成了东北本土第一代诗歌创作群体。正如孙旸在一首诗所描绘:“金风徂暑火西流,朱邸开樽月满楼。筵为穆生常设醴,人同宋玉又逢秋。窗临碧树寒声早,座近青莲夜色幽。伫看小山丛桂发,不须招隐更来游。”可见当时的盛况,可见他们玩得真是很嗨。
那时的高塞只有20岁左右,他帅气清爽,儒雅谦和,他是皇子,他又不是皇子,他是公爵,他又不是公爵,他只是大家的知心朋友。
宗人府胡同的公爵府里,有“月满楼”、有“碧树”、有“青莲”、有“小山”,这里酒兴与诗情一同飞扬。
难怪高塞大哥肃亲王豪格的一位直系后人说:“盛京的辅国公府也是大观园,我六叔祖爷爷也是贾宝玉的原型之一,曹雪芹一定知道他的故事。”
贾宝玉在大观园营造了一个诗人创作的自由天地,他与高塞好像有相似之处。大观园里的写作带有自娱自乐性质,而公爵府里的写作就没有那么简单。
还不只是在公爵府里写诗唱和,高塞还投资专门为这些人建立了文学院—“东平书院”。苗君稷在他的一首诗的序言中说“辅国公去城东数里,植柳种菊白屋中,起绕以垣,曰东平书院。”这应该是东北地区较早的文学院了。
那么,这个东平书院在沈阳什么位置呢?
这就要先说一下“东园”。
“东园”,在陈梦雷(1650-1741)的《东园泛菊》里有明晰描述—“梁苑当年菊,犹开沈水涯。”“梁苑”,原指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的宫苑,这里喻指高塞所建的“东园”,其实诗的标题已经标明了。而“沈水”,据为这首诗作注的著名学者孙丕任先生说“这里的沈水就是万泉河,也叫小沈水。”
那么,“当年菊”是当年谁种的菊?别忘了苗君稷在前面说过的话,他说“辅国公去城东数里,植柳种菊白屋中……”万泉河在城东,都城距万泉河5华里左右,也正是苗君稷所说的“城东数里”。《沈阳县志》上说“万泉河在邑城抚近关之东……”也与苗君稷说的“城东”相吻合。
可见,东平书院与东园应该在同一坐标上,或重合,或相邻。有学者著文,干脆将“东平书院”与“东园”说成一个地方,似乎也应有他们的道理。
我在苗君稷的作品中,发现高塞在东园附近还建造了一个“淡园”,他在那里专门培育海棠。比如这首《重游辅国淡园咏海棠》“重来梁苑未春残,垂柳阴阴问药栏。却植海棠花正发,低回风雨出关寒。”前面我们说过“梁苑”即“东园”,那么,从这首诗的内容看,“淡园”与“东园”应该在大致相同的方位上。
种菊,又种海棠,可见高塞对待这些诗人的良苦用心。他自己是诗人,他知道诗人喜欢“海棠”与“菊花”。
大学者陈梦雷是康熙二十一年四月被流放到沈阳的,此时高塞已去世12年。但东园还在,东园里高塞当年种下的菊还在。
也就是说,在顺、康年间,东园、淡园和东平书院,是盛京城的著名景点。东园与淡园何时消失的不清楚,但似乎从此人们在万泉河畔建造花园成了风气,到清末民初先后出现了“半可园”“鸥波馆”“万泉园”等。到了1907年,终于成为万泉公园。

1910年的沈阳万泉公园
1918年出版的《沈阳县志》这样描述——“万泉河在邑城抚近关之东,源出观音阁之涌泉,西流入东水栅栏至魁星楼,过虹桥而南注入南水栅栏,与二道河会,俗呼小河沿,即小沈水也,清波一泓,珠泉万孔,而四时不涸又名万泉河。河之上水草丛生,荷花茂盛,为夏日游人避暑之地。”
万泉公园很可能是从高塞所建的东园、淡园一路走来。而这一带,竟也成了清诗在沈阳的繁华之处。有清一代沈阳的诗歌创作,在这里几乎贯穿了始终。
陈梦雷在这里写下了《沈水春游》、戴梓在这里写下了《春日泛舟沈水》、纳兰常安在这里写下了《沈水》、缪公恩在这里写下了《万泉河步月》、缪公恩的曾孙缪润绂在这里写下了《沈阳百咏》……
博学的诗人陈梦雷应该是知道诗人高塞的,他甚至应该是专程来东园凭吊高塞的。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也希望遇到高塞一样“乐与文士游处”的人。果然,他很快遇到了奉天府尹高尔位(1625-1701),他得到重用,并完成了大型文化工程——《盛京通志》。
我一直认为高塞中后期开始自觉地入世了,他开始为王朝服务了。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顺治帝在临终前写下的《罪己诏》里,痛心地自责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弟兄,流露的是骨肉亲情。他说:“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在这些受委屈的皇子皇孙中,自然包括他的六哥高塞。
弟弟写完《罪己诏》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当哥哥的步伐则更加坚定了。
康熙即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高塞多次应召回京。在苗君稷的《焦冥集》里,至少有五首诗是送别和想念高塞应诏进京面圣的。他回京去做什么,又带回了什么样的使命?康熙不会仅仅是因为想念伯父才下的诏书吧?那么,下的是什么诏书?这些似乎不大好考证,但幕后的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
在春雨如酥的日子,在夏雨纷纷的日子,在秋风薄凉的日子,在冬雪飘飞的日子,在东园在东平书院,情感解冻了,隔阂消除了,诗歌一天一天长大,并且向着民族大融合的方向日益成熟起来。
9
有趣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函可、苗君稷、孙旸等人的诗句里,已开始频频出现“圣主”“丹诏”“丹书”“紫微”的字样,表达了诗人们对朝廷的尊崇。苗君稷甚至还写了一篇《恭和圣制旌射诗》—“宿卫龙孙近古风,得心应手不知弓。一时角逐褒天语,中外争传召虎雄。”有尊敬,有赞美,有自己人的感觉。说明经过高塞的努力,最终,让他们摆脱了个人恩怨,能够客观评价新政权对平息战乱和天灾的努力,对人民休养生息政策的兑现,对国家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
后来,蒋鑨去云南大理做了地方官;陈维崧被授官翰林院检讨,编撰了《明史》;函可坚守着僧人的使命,积极开法于关东名刹,同时,
创办了东北历史上第一家诗社“冰天诗社”,将文学结社的风气带到了盛京,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芝兰诗社、荟兰诗社等众多诗社,函可因为创作成就卓越,最终成为一代诗僧;苗君稷出版了两卷本诗集《焦冥集》,如实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与变革;孙旸回到老家,晚年出版了《荐庵集》,与蒋鑨、陈维崧、函可、苗君稷一样,为清诗的产生、发展、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清初的诗坛进入了良性的生态。至此,高塞感召文化人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康熙八年,他由辅国公晋封为镇国公。有人说他可能因为在剪除鳌拜的搏杀中立了功,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感召知识分子的政绩却是历历在目的。
高塞受封镇国公,是他的兄弟当中除了大哥肃亲王豪格、五哥承泽亲王硕塞、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外的最高爵位。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的爵位还应该升级,因为康熙成年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编辑《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等等,高塞的才华将尽情得以发挥。
回到北京之后,大家庭的热闹氛围似乎不复存在了。
一奶同胞的十妹受封县君,嫁与一等公瓜尔佳氏辉塞,已于顺治十八年去世;十三妹嫁与副都统瓜尔佳氏拉哈,已于顺治十四年四月去世。同父异母的四哥辅国公叶布舒、七弟辅国公常舒、十弟辅国公韬塞虽然还在,虽然兄弟们会经常宴请他,虽然他也经常回请,但他们毕竟不是诗人,能说的心里话不多。如果五哥承泽亲王硕塞活着就好多了,硕塞除了能征善战之外,诗歌绘画也好,他画的《奇峰飞瀑图》得到大学者高士奇的盛赞。
兄弟11人、姐妹14人,如今却显得如此凋零。高塞尽管超然于世事,但伤感多少还是有的。他毕竟是诗人哪。
按说,他应与四哥叶布舒更亲近一些,叶布舒的母亲、皇太极的庶妃颜扎氏是高塞嫡妻的姑祖母。
康熙九年四月的一天,应四哥叶布舒的邀请,高塞参加了叶布舒长女与御前一等侍卫瓜尔佳氏黄海的隆重婚礼。那一天,他见到了七弟辅国公常舒、十弟辅国公韬塞,侄子温郡王猛峨,还有太祖努尔哈赤一支的各位亲王和郡王、贝勒、贝子。康熙帝赐宴,热闹非凡,但高塞对热闹一向没有多少兴趣。
高塞还是想念那些诗人,他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府上,高士奇、沈荃、蒋鑨、陈维崧都在大客厅里等着他呢。
但话题聊完的时候,在诗人们陆续散去的时候,他会再度陷入深深的寂寞。
在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二十二日夜间,高塞面向盛京的方向,悄然逝世,享年只有34岁,他还是个青年,太可惜了。他留下5个儿子,长子靖恒在5个月后,降袭辅国公。康熙赐给高塞的谥号为“悫厚”,意即“朴实厚道”,这也是对他人品的概括。
皇帝赐给谥号,是对死去臣子的恩封,在高塞的兄弟中只有大哥豪格、五哥硕塞、十一弟博穆博果尔被赐了谥号。看来,康熙还是认为六伯父业绩更突出一些,这就是前面讲的在感召知识分子方面做出的贡献。
10
这时,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物再度在中国文学史上登台亮相。
当年备受高塞恩惠的孙旸,将他留下的15首诗编成《恭寿堂集》,并带到了苏州,渐渐地,在诗歌昌盛的江南地区流行起来。最后再度回到北京,流传到高塞族曾孙怡亲王弘晓府上。
一时,在王公大臣之间传阅开来。
弘晓除了是诗人,还是大藏书家,乾隆是时常要到这个堂弟家看书的。据说,乾隆就是在弘晓家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这次又看到了《恭寿堂集》,他没有禁止,这就基本上等于公开出版了。
高塞保护了诗人,感召了诗人,客观上也将清诗扶上了骏马。
作为清诗的开拓者,高塞在清初的声望很高。康乾时期,好多作家都在著作里高度评价他的诗作。如康熙年间王士桢的《池北偶谈》、乾隆间诗人法式善的《奉校八旗人诗集题咏》、乾嘉年间礼亲王昭琏的《啸亭杂录》、铁保的《熙朝雅颂集》、清末民初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杨钟羲的《雪桥诗话》、民国徐世昌的《晚晴籍诗汇》,都对高塞的作品给予点赞。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作为御前一等侍卫,纳兰性德随康熙东巡来到了沈阳。他去没去东园不知道,去没去东平书院不知道,但他却专门写了一首名为《盛京》的诗——
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庙社灵风肃,豪强右族更。明明开创业,休拟作陪京。
这是纳兰性德随侍清圣祖康熙皇帝巡行奉天、吉林,到兴京永陵祭祖返程驻跸于盛京时所作。
纳兰性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清诗出现了高峰。而从诗歌传承“谱系来看”,纳兰性德应该是高塞近支嫡传的“诗二代”。
论起来,纳兰性德应叫高塞一声舅舅,他的母亲爱新觉罗氏是高塞十二叔英亲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的十二子)的女儿。而高塞的母亲又是来自于那拉氏家族。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准确辈分,但也应算是另一层族亲。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高塞逝世于康熙九年(1670),在时间上两人有15年的交汇点。康熙初年,高塞回京后诗歌影响已经名满天下,特别重视子弟教育的弘文院学士的明珠应该带儿子纳兰性德到高塞府上求见,让他怯生生地叫高塞为舅舅,然后,一面喝茶一面大谈特谈诗歌创作。
于是,后来中国就出现了“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性德。
诗,是自由的产物,在不自由的清代初年,高塞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创作活动积极影响了统治者,让他们充分认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样,顺治本人也写诗了,康熙也写诗了,以至于后代皇帝们也大都写了诗,皇子皇孙也纷纷爱上了诗歌写作,到清末,宗室诗人总数高达89位。
这等于说高塞用智慧为诗歌的自由之门打开了一个门缝儿,诗人蜂拥而至,在沈阳地区先后涌现出康熙、纳兰性德、陈梦雷、戴梓、戴亨、乾隆、纳兰常安、缪公恩、裕瑞、金朝觐、多隆阿、魏燮均、缪润绂等诗人,他们或世居沈阳,或客居沈阳,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黄金期基本上都是在沈阳,而且写出了无愧于这座城市的金子一般的作品。纳兰性德、陈梦雷、戴梓、缪公恩、金朝觐、缪润绂的诗歌,在清代诗歌“国家队”里也是上乘水平。
特别令人惊喜的是,关内的大诗人与之遥相呼应,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沈德潜、袁枚、郑板桥、龚自珍等泰斗级别的大诗人纷纷拿起笔来,在有限的自由度之内,由地下转为地上,大大方方地创作。
尽管“文字狱”贯穿清代始终,尽管清诗受到恐怖式限制,具有先天不足的题材单一、技巧过度,艺术大于思想的弱点,但在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出现了大批量的超过元明两代,足以下启近代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后劲的作品。有人说清诗与唐诗、宋诗呈鼎足之势,这个结论似乎问题不大。
至少从这个角度上看,高塞功不可没。
300多年来,沈阳万泉河一带,特别是建成公园以后,这里始终是个诗意盎然的地方。总有好奇的人来到这里感受诗歌,并且寻古探幽,试图找到先贤们的踪迹,哪怕是一丝一毫。我就比较关心,在62万平方米的公园区域内,究竟哪个地方是高塞建造的“东园”“淡园”和“东平书院”?究竟哪一丛菊花、哪一株海棠是高塞手植的那些菊花与海棠的后代?中秋将至,菊花就要飘香了,选个好天气,再去细细地观赏一番……
编辑:赫明
责任编辑:刘新阳
爱新觉罗宗谱网
2023年9月4日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