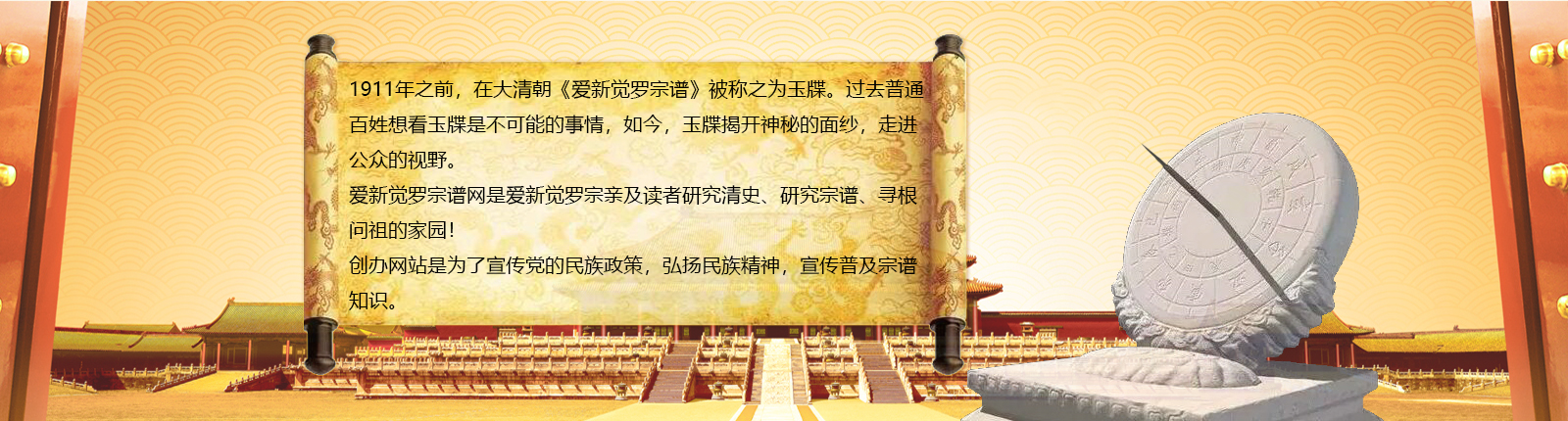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文:定宜庄 (红缨满洲)
文:定宜庄 (红缨满洲)
在我国东北谙族和与之关系甚密的蒙古等民族的原始宗教史上,树神崇拜占据的位置相当重要,这本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这些民族形成初期,东北广袤的大地上曾覆盖着十分浓密的森林,亦即满语所谓的“窝集”、 “渥集”。直至清代,文献中还有这样的描写:“东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渥集之故。渥集者,汉语老林也。长白山阳,亘混同江、宁古塔、兴京之南,树海绿天数千里,万产愤盈,参蜜貂鹿,利尽表海”。这里说的是东北的东部,亦即满、赫哲等民族的聚居区。而在东北西部的兴安岭一带,更覆盖着无边无垠、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人们用“黑森林”来形容它,可见它的幽深浓密。丰饶神秘的大森林,是养育这些民族的摇篮,人们依赖它,同时也畏惧它,对森林的崇拜,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视念和仪式,就是从这种敬畏之中产生,并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应当指出,这些崇拜和仪式,并不仅存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中,有着形形色色崇拜树神仪式的遗存,它表明满、蒙等民族的树神崇拜,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探讨从树神崇拜视念演变而来的各种仪式和习俗,特别是满族、蒙族等民族独特的习俗,是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01、生命树、氏族树和求子仪式
远古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树,他们对树木充满感激和依恋之情,我们可以雅库特人(雅库特人——西伯利亚南部的居民。自称“萨哈人”,主要分布在今苏联贝加尔湖东南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等地。)的原始神话为例:
“开地之初,在大地的黄色肚脐上,耸立着一棵大树,树上有八条繁茂的树枝,树干一直穿过三层天,树皮和树疖都是银的,树液闪着黄金色的光芒,果实像巨大的酒杯,树叶像张张马皮。从树梢经过树叶流淌着神圣的黄色泡状液体,人们饮过它就得到了大福”。
在这个神话中,神树是养育人类、赐福人类的生命之树,这是人们对树木的最根本也最原始的观念,他们把树看得就像是养育自己的母亲,东非万尼卡人就认为“每毁坏一株椰子树,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因为椰子树给予了他们生命和营养,正如母亲对孩子一样”。
人们因树木的长寿和生生不息的繁殖力而崇拜它,渴望借助它那超人的神力。赫哲人说,天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神树,上面栖息了众多的“奥米亚嘎沙”,即状似雀儿的“魂鸟”,在投胎到母腹之前,它们都栖息在“奥米亚莫尼”即“魂树”的枝杈上。他们还认为,周岁以内的婴儿相当于一种抽象之物,倘或不幸天亡,他的“魂鸟”还会飞回到神树上,等待下一次的降生。因此,赫哲人从不把死去的婴儿土葬,而是进行树葬,举行仪式时,要将系在他身上的丝线扯断,意味着死婴的灵魂中止了与母体的联系,重新变为鸟雀飞返神树上。这种对树木繁殖力的崇拜,大同小异地存在于世界的许多民族之中,而与赫哲人上述说法最相似的,恐怕要算毛利人的图霍部族了,他们认为树木有能力使妇女多生子女,这些树木是神话中祖先的脐带,就像所有刚出生婴儿身上都挂有脐带一样。可见赫哲人所谓的绿线,就是这种脐带的象征物,它每每出现于满族、鄂温克、鄂伦春等族有关生育和丧葬的仪式中,象征着生命与母体的联系,而这里所说的母体,就是树木,树木被人们看成为母亲,又进而看成为祖先,所以,当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这多子多孙的母亲之树,便被人们与氏族联系起来,奉它为氏族之树了。
氏族树是祖先的象征,也是保佑后代子孙繁衍的神物,种种求子仪式,即是这样产生的,这可能是人们向神树乞求的最直接的目的了。求子仪式在东北诸族中存在得十分普遍。赫哲妇女年逾三十尚未生养者,便认为自己没有“转生的灵魂”,必须请萨满举行找魂求子的仪式,称之为“提雀”,以求得“魂鸟”投胎。满族所祭的“佛朵妈妈”,其实也出于同一根源,只是被后世涂抹得太过分罢了。
“佛朵妈妈”是满族萨满教中最重要、供奉也最普遍的神灵之一。满族的民间传说,或谓她是明代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小妾的化身,因于努尔哈齐有恩而成为满族的祖先神;或将她称为“万历妈妈”,附会为明朝万历皇帝的母后。而实际上,她的全称是“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就是“求福柳枝子孙娘娘”,我们推测,即是由对柳树的崇拜而演变来的祖先神。
“佛朵妈妈”的形象,除有些姓氏悬有木制或帛制的神偶外,多以柳枝为女神象征,俗称“柳枝祭”。选择柳树作为神树,可能因为柳为当地最普遍、最常见的树种,也可能取其春日最早发芽,且插到哪里都能成活的特性。与柳的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肯定在金代女真人之前即已有之,满族的崇柳,很可能是受到金代女真人的影响。总之,在萨满教的神谕中,是流传着不止一个柳叶生人的传说的: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世上还刚刚有天有地,阿布卡恩都里(注:满语,意即天神)把围腰的细柳叶摘下几片,柳叶下便长出了飞虫、爬虫和人,大地从此有了人烟。直到今天,柳叶上还好生绿色的小包,包里生虫子,就是那时候阿布卡恩都里留下来的。”(珲春那木都鲁氏神谕)
又如:
“在古老又古老的年月,富察哈拉祖先居住的虎尔罕河突然变成虎尔罕海。白亮亮的大水淹没了万物生灵。阿布卡恩都里用身上搓落的泥做成的人只剩下了一个。他在大水中漂流,眼看就要淹死了,忽然水面漂来一根柳,他手抓柳枝漂进石洞,才免于淹死。柳枝化作一个美女,和他配夫妻,生下了后代。”(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家祭神谕)
这类神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柳在女真以至后来满族的视念中,与氏族繁衍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测,满族早期的氏族树,可能就是柳树。金太祖完颜阿古打以及后金太祖努尔哈齐起兵时所祭神树皆为千年古柳的传说,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一个证据。直至近世,在辽南如岫岩县以及黑龙江省的某些地区,还有人家在庭院栽柳以为神树,并以为祭祖之所,吉林珲春的满族在祭天祭祖时,也要在山坡或野外,树柳枝以为神位。

不过,满族人民祭“佛朵妈妈”,其主要目的还是求子,是求她保佑家族的繁衍。岫岩满族在求子时,于祖宗板的左侧供“佛朵妈妈”,有位无像,两面墙壁上挂“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三尺,即“子孙绳”,大概就是那脐带的象征物了。祭时,先将屋内的“索子口袋”打开,将袋内“子孙绳”拉出,系于房门东侧竖立的柳枝上,分食祭肉以后,妇女儿童围坐于柳枝周围,或跪于“索子口袋”之前,举行祈福求子的祷祝。这是满族民间保存较完整,流行也较普遍的仪式。在清代皇室及贵族中,这种祈福仪式要比民间繁琐远甚,但以绿线系之于柳,希冀借助柳树繁茂的生命力来保佑家族繁衍的基本视念,却是不变的。
除对柳祭的崇拜而外,在东北新满洲的一些部落中,还流行着对橡树、桦树等不同树种的崇拜。清朝初年从乌苏里江东迁到宁古塔的新满洲郭合乐氏,即供奉“他拉罕妈妈”,供奉时要在树上悬挂一桦皮盒,可能即是由对桦树的崇拜演化而来的。总之,“佛朵妈妈”、“他拉罕妈妈”,以及锡伯族的“锡利妈妈”等等,最初可能都是不同民族、部落所信奉的不同树种的。“氏族树”,是养育人们,保护他们人丁兴旺的“母亲树。”

02、祭神的圣所
起初,原始人是把每一棵树都看成为有灵魂的东西进行膜拜的,他们认为树木就是神灵的身体,所以一点也不敢伤害它。后来,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他们逐渐能从具体中概括出抽象的概念来,树木便被他们理解为神灵往来居住的处所了,他们往往认为神的灵魂寄居在某丛、或某棵大树中。例如,古代蒙古部落极为崇拜枝叶茂盛的“蓬松树”,因为萨满说,他们最崇拜的守护神宝木勒和精灵,就居住在“蓬松树”中,每逢部落有重大活动,人们都要向树上的宝木勒祈祷,围绕着“蓬松树”唱歌。神既然居于树上,所以祭神的物品,就都是悬挂于树上,女真人自金代起,就有将牲畜皮挂在树上祭神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相沿至明代,海西女真人,父母死,祭祀用马而食其肉,“张皮鬣尾脚挂之”。据许多民族学家的调查和记载,这种习俗广泛存在于西伯利亚的各民族中,他们杀马祭神,就把马皮张挂在桦树上。
原始人在神树下举行各种仪式,树林便成为他们最初的宗教圣所。前面提到新满洲郭合乐氏供奉的“他拉罕妈妈”,据说就是住在神树上的,人们在秋祭第一天,由族长率领全族跪拜在神树前,宣读族规;《元朝秘史》中提到蒙古人结盟、交友,也都在“蓬松树”下起誓、舞蹈,显然也是将其视为最神圣的处所的。而在汉魏至南北朝时期曾十分活跃的著名古代民族——鲜卑人,也曾有过“大会蹛林”的习俗,据颜师古的解释,“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虽然具体的仪式已无法探究了,但以林木为祭祀之所,则应是无疑的。此外,在朝鲜族农村尚有遗留的萨满教仪式中,也有选择神树作为守护神,或者在树下设祭坛来当作神堂的作法。
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后来离开了他们祖先所居住的原始森林,迁徙他乡了。但是,以树木当作祭祀场所的习俗,却一时难以更改。从狩猎转向从事农耕、畜牧的达斡尔人和部分鄂温克人,每逢举行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奥米那楞节会”(一译作“斡米南节会”)时,要立120株树木来象征他们已经离开的森林,以作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上面提到的鲜卑人“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没有丛林,用一根木头、一丛树枝来代替它,形式越来越简化,但也越来越固定,并且因为是从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而越来越隆重,而它本来的意义,它的起源,则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于是就产生了种种的臆测和穿凿。满族的杆祭和蒙古族的祭敖包,大概是最典型的两个,杆祭的内容要复杂一些。这里我们先谈谈祭敖包。著名的蒙古学学者海西希曾指出,这是蒙古族“最古老而独特”的习俗。
敖包一译作鄂博,原意为土包或堆砌物。祭敖包时,要选择一个比较宽阔的,阳光充足的高岗,用土或石块垒成底座圆、顶端尖的石堆,并在中心植树。由于敖包的起源十分古老,喇嘛教又对它的祭祀礼仪进行了修饰涂改,致使人们已难以探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怀疑在喇嘛教征服蒙古诸部之前,是否曾真的有过这种风俗存在了。我们推测,这种用土或石决堆砌而成的石堆,应是山的象征物,而石堆上所植树木,有时也用一丛柳枝代替,是蒙古古代曾供奉的神树的象征,山与树,原是蒙古祖先祭祀的场所,存草原上,敖包也的确是被人们当作祭坛,当作祭神的场所的。
鄂温克人供奉的“敖包树”,也许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一个佐证。在内蒙阿荣旗查巴奇村的“敖包”就是一棵大树,在鄂温克萨满的视念中,它是神灵所居和寄享之地,每逢干旱求雨时,就要用牛或猪向它祭祀。可见,它与蒙古古代神灵所棱的蓬松树,其含义是差不多的。而在达斡尔人定居的地方,敖包是在老树周围堆积石头而成,人们就将老树称为神树,[14]这很可能是从神树到敖包转化问的一种过度形式。
蒙古人对敖包十分敬畏,将其视为神圣之物,“峰岭高处,积乱石成冢,名鄂博,谓神所棲,经过必投以物,物无择,马鬣亦可”,“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番人见之多下马。”即使当喇嘛教对它进行修改之后,人们也仍然将它看作本地神灵的聚集场所。辽宁阜新蒙古族的祭敖包,就包括了“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求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牧群兴旺;求人间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岁岁太平”的诸多内容。总之,敖包作为祭坛的特点,是始终不变的。

03、通天之桥
超乎一切神灵之上的造物主“天”的形象,是较晚才出现的。一般来说,它是人世间出现了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权力以后的产物,也是人们思维能力大大发展的结果。抽象的“天”与原始宗教中哪些山、水与动物等从具体产生的神灵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在成吉思汗和努尔哈齐的崛起过程中,“天”的感召力、感慑力都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天虽高高在上,威力无比,离开了与人间的沟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既然不能上天,不能直接与天交往,就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充当这一媒介的代替物,于是,鸟与树,便充当了这一角色。
原始人本来就有树能通神的说法。生活于西伯利亚不毛之地的涅吉达尔人,每在祭祀前,要从森林中选出一棵落叶松,将它的枝杈砍光,在上面刻出脸庞,向它献祭。爱奴人的祭祀也大抵相同,他们选定一根上面带有许多小舌头的刨光的木棍,当成向神祷祝的传话人,叫做“伊脑”,意思是“树的舌头”,将它缚在神树上,然后对它祈祷,希望它把自己的虔诚传达给冥冥中的神灵。而当“天”出现以后,这种通神的能力便正好用来通天了。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著名的扶桑树,就是起通天作用的。在满族神话《通天桥》中,这种作用表现得则更加明显。据说,阿布卡恩都里(满语,意即天神)为了制服地下魔鬼耶路里,用霹雳击毁了通天桥。于是,来到天上的人们都回不到地上了。阿布卡恩都里选了一棵最高最大的树,让人们顺着树干下到地上。回到地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没有来得及回到地上的,就留在天上变成了星星。……后来,人有什么向天神的要求,便通过大树告知天神,因为树很高,所以天神只要稍微弯弯腰便知道了。神话还解释说,这就是满族祭树立杆的由来。
在满族萨满教所谓的世界三大界——上、中、下界之间,据说就是由神树相连接的。神魂附体的萨满在这棵树上爬上爬下,上天入地,既与天冲交往,又与魔鬼盘旋,鸟儿则是他的助手。在这一说法里,已把树、鸟与萨满三者间的关系,描述得相当清楚,它对我们理解满族的杆祭,是有一定作用的。
树的功用既然又较前增加了一重,那么全由一棵树来承担,就未免太繁重了,于是在有些民族的神话中,就把神树的数量增加到三棵,五棵、七棵,甚至更多,与他们心目中天的层数或某些神的数目相对应。这些神各有分工,有的主管生命和繁衍,有的是通天之桥,还有的专司智慧等等,就像众神各司其职一样。在满族中,由柳树幻化而来的佛朵妈妈与通天的神树之间的分工,也许就属于这一种。

04、对满族祭神杆之俗的几点探讨
神杆,满族称索罗杆。满族人家在庭院的东南隅,置一根长约丈余的木杆,上面置斗,盛肉以饲乌鹊,每逢年节或宗族聚会,要宰猪以祭之,这是神杆最普遍的形式。
神杆并不仅存在于满族之中。早在《后汉书》中,就已记载过三韩诸国“邑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的仪式;金代女真人也有这种习俗“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元朝的蒙古人也曾有“以杆悬肉祭天”的作法。不过,这种祭祀习俗确实在满族中存在得最普遍,无论是清代沈阳、北京的皇宫和堂子,还是东北寻常的百姓之家,院中竖立的索罗杆是不可或缺的,它简直成了满族萨满文化的特征,甚至是满族人家的标志。
至于祭神杆的起源,清人即已注意到并有不少解释。有人因其形制如长矛,称其“当日军行无定居,每祭天地,则竖一杆为神凭依,后世因之不敢易;”也有人说仿满族先人采参之器“立杆院中示不忘”;还有人说“立杆祀天也,以高为贵,取其上与天通”,等等,虽然也许不无道理,但毕竟多属臆测。
我们认为,杆祭习俗,实起源于对神树的崇拜。从满洲立国后才逐渐纳入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大多来自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一带的“新满洲”的祭祀仪式中,我们往往可以找到从神树崇拜到杆祭之间的,作为过渡的某些表现形式,它们对我们探讨神杆的起源,是颇有意义的。
首先,许多新满洲部落,还仍然以树作为祭祀对象。新满洲中伊尔根觉罗氏所祭的,是“祖先早年手植之树,或昔年祖遗森林”,祭时要在日将出时,将先祖木像请到树前,面向东北,将净纸一张挂在树上,拈香后,置猪于树前,先“领牲”(“领牲”——见《吉林乡土志》第271页。将祭猪绑卧神前,以酒注入猪耳,猪感痛痒,乃摇头摆耳。家人见状,即指为神来飨用,是谓“领牲”。),然后以盅跪接猪血,用香蘸血上祭,解为七部挂于树上,等等。这一系列步骤,与其他满族部落举行杆祭时的做法是相同的。又如依兰的满族“家家供树一株,旁列木人一个,为神,日色勒可嘎呢,又刻二小木人,名朱那雅(译二使役),亦春秋宰猪祭之,当日在树下煮熟,村邻共啖……”

还有一些满洲部落,已从直接祭树转化为祭祀,但仍然在野外,如吉林永吉乌拉街的满族,每年要到山上去祭神杆,祭完后就将杆子立于山中。还有的,所立神杆尚不止一根,“凡巫家必置多杆于宅西祖祠之前,上刻鳞虫鸟兽之类,多少不等”,看来,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些部落开始向较固定的杆祭过渡,家家屋前“立木一根,以此为神”,每逢喜庆或遇疾病则祭之,若病不愈,便将此木掷于门外,“以其不灵也”,以后若专必要,再新设一根。其实,这种更换神杆的做法,在“佛满洲”中也偶可见到。
从上述这些以杆为神的习俗来看,大约满族也曾如蒙古族一样,有过神灵栖于大树上的视念,因而,神杆亦如敖包一样,很可能是尚未脱离原始状态时的人们的祭坛,从杆祭在满族萨满教中位置的重要,从合族老小敬而拜之的情况,也可证实这一点。
至于神杆所祭的神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落中,也是有变化的,我们认为,它最初是祖先神的凭依之物,这大概来自死者灵魂回返氏族树的视念。以神的祭祖的例子,在满族中是不胜枚举的。“寻常庭中,必有一竿,竿系布片,曰祖先所凭依,动之如掘其墓。刲豕,而群鸟下啖其余脔则喜,曰‘祖先豫’,不则愀然,曰‘祖先恫矣,祸至矣’。”许多满族都将神杆称为“祖宗杆子”:“满洲宅院中立杆一,高丈余,名索莫杆,又曰祖宗杆”。直至近世,在许多佛满洲的祭杆仪式中,祭祖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至于后来在满族特别是满族宫廷中最为流行的“以杆祭天”的固定礼俗究竟起于何时,史料既不见记载,就很难查考了。从上面列举的新满洲诸多祭杆形式推断,它大概是努尔哈齐建立后金,各种礼仪开始制定与完备之后的事。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必然受到过曾建立政权,有过正规仪礼的夫余、金代女真等立杆祭天的影响,将神杆赋予祭天的含义,以及产生诸如“通天桥”一类的神话,恐怕不会早于这个时期。
以杆祭天,成为宫廷隆重的大礼,每逢出征作战,努尔哈齐与他的后代们都要聚集在神杆前,乞求天的护佑。皇家的礼仪对于满族的百姓,当然不会没有影响,于是,满族部落中形形色色的祭树、杆祭仪式,便纷纷向这种固定的礼仪靠拢,并大体取得了一致。总之,杆祭是从远古时代神树崇拜发展而到神木祭祀,又进而演变为具有特定形制的神杆的,它适应了满民族从森林中的渔猎部落到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条件的变迁过程。与此同时,它伴随着满族社会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萨满教文化的发展,逐渐从祭祖演变为祭天,成为萨满上与天通的桥梁和媒介,又进而成为满族初兴时期统治者的思想武器之一。至于以神杆饲鹊的做法,涉及到满族神鹊崇拜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中已无暇讨论。但鸟栖于树,本是最常见的自然现象。鸟是萨满的助手,将其与神杆结合在一起,本是很自然的事情。祭神有杆的仪式,内涵是相当复杂丰富的,它包含了有关神树崇拜的各种观念,这正是满族形成时期吸收了各种不同成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一个反映。神杆祭祀将这一切不同的观念和习俗融合为一体并使之定型化,终于成为满族萨满教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仪式之一。
(内容来自《北方民族》1989年第1期)
爱新觉罗宗谱网转载
2024年5月2日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