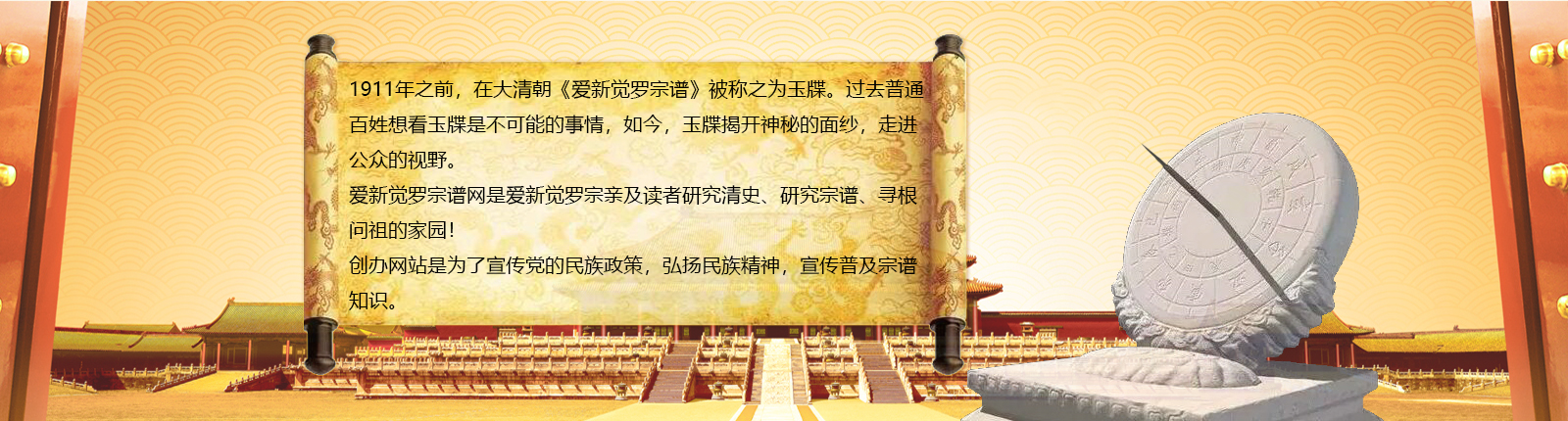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众所周知,清朝皇室的姓氏是“爱新觉罗”,这是后金—清朝的国姓,那么,爱新觉罗与觉罗是什么关系?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爱新觉罗”四字旁有注云:
“爱新,华言金也”,“觉罗,姓也。”
这已经说得十分清楚,“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其源流姓氏就是“觉罗”。
佟悦先生在其1997年发表的论文《清入关前的爱新觉罗宗族》中明确指出,
“爱新觉罗”的正确解释应是:“爱新”并非完颜金的“金”, 而是后金的“金”。将其冠于原姓氏“觉罗” 之前, 表示本氏族是以国号“金(爱新)”为姓氏标志的觉罗氏。”
“采用新姓氏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将汗王近支亲族从同姓中分离出来。姓爱新觉罗氏者均为努尔哈赤曾祖福满后裔, 即所谓“六祖子孙”。但与努尔哈赤同姓者非止这些人。因为孟特穆后代不可能只福满一个支系, 况且尚有孟特穆叔伯兄弟后裔”。“孟特穆,又译作猛哥帖木儿。”
佟悦先生的论述已经十分清楚,“爱新觉罗”姓氏只用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的子孙,“爱新觉罗”,是以国名加上源流姓氏,其源流姓氏是“觉罗”。而其他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父系同宗的人的子孙,因为血缘关系已较远,他们的姓氏不是“爱新觉罗”,而是诸觉罗氏,其源流姓氏亦是“觉罗”。清代满洲人姓氏最常见的组成,是以居住地名加上源流姓氏,如居住在乌拉、姓觉罗者,其姓氏为乌拉觉罗。
由此可见,广大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父系同宗的人的子孙,而非福满子孙者,其姓氏应为爱新觉罗以外的诸觉罗氏。这一点,对于研究爱新觉罗家族的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启孮先生在其1988年发表的论文《爱新觉罗姓氏之谜》中明确指出,
“爱新觉罗一姓, 其实姓是觉罗。‘爱新’只是‘徽称’。”
“爱新既是徽称, 而觉罗才是姓; 那么, 满洲姓觉罗者实不在少数。除爱新觉罗外, 尚有伊尔根觉罗、乙林觉罗……等, 则知觉罗氏实为满洲一大族。”
“觉罗氏, 实即金代的交鲁氏”。
对于“爱新觉罗”作为清朝皇室的姓氏,金启宗先生阐述地已十分清晰,“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其源流姓氏就是“觉罗”。姓“爱新觉罗”者,其祖先姓氏就是“觉罗”,其与满洲人中其他“觉罗”,如“伊尔根觉罗”、“乙林觉罗”,其源流姓氏是相同的,均是“觉罗”氏。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父系同宗的人的子孙,其为福满子孙者,其姓氏为“爱新觉罗”,其非福满子孙者,其姓氏为“爱新觉罗”以外的诸觉罗。
“爱新觉罗”,满语写作aisin gioro,aisin是“金”的涵义,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加上去的。在这之前,爱新觉罗家族的姓氏就是觉罗,满语写作gioro ,也可以简写为goro。 那么,gioro这个词来自哪里呢?用阿尔泰语无法解释,在满语中可以找到的本义是“远支,血缘关系远”。如goro niyalman的涵义是“远亲”,niyalman的涵义是“人”,并没有“亲戚”的涵义,“远亲”的涵义来自goro。西方学者在对马来语的研究中,发现在马来语中存在一个词汇galor,涵义是“追溯起源,调查祖先或经历”,还有一个与之发音相近的词汇kalour,指“马来人中掌握宗教音乐、与王族有亲属关系的贵族”(罗艺峰等2002)。
不仅如此,在马来语中,susur的涵义是“追溯起源,从它的末端追寻它的起源,事物的起源和历史”,susur galor的涵义是“家族关系”(罗艺峰等2002)。 而满语susu有“祖籍”的涵义,goro有“远支,血缘关系远”的涵义。在与家族渊源相关词汇上,满语与马来语竟然是一一对应的!
马来语与印尼语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都源于祖居地在印度尼西亚廖內省的马来族(狭义)的语言,只是因为分别作为两个国家的国语,在涵义和拼写上略有差异。
与goro在满语中的本义“远支,血缘关系远”相对应,在印尼语中,gara的涵义是“父亲或母亲双方的真正后代”,kerabat的涵义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与爱新觉罗家族的源流姓氏gioro相对应,在印尼语中,galur的涵义是“世系,谱系树”,keluarga的涵义是“家族”。
鲁凯族是台湾原住民中的一个族群,其语言与马来语、印尼语同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
与爱新觉罗家族的源流姓氏gioro相对应,在鲁凯语中,cocongolra的涵义是“子嗣,系谱,祖系”。
下表列出了在家族渊源相关词汇上,满语与南岛语的对应关系。
表:在家族渊源相关词汇上满语与南岛语的对应关系
|
语言 |
词汇 |
涵义 |
|
满语 |
gioro |
清朝皇室源流姓氏 |
|
满语 |
goro |
远支,血缘关系远 |
|
马来语 |
galor |
追溯起源,调查祖先或经历 |
|
马来语 |
kalour |
马来人中掌握宗教音乐、与王族有亲属关系的贵族 |
|
印尼语 |
galur |
世系,谱系树 |
|
印尼语 |
keluarga |
家族 |
|
鲁凯语 |
cocongolra |
子嗣,系谱,祖系 |
不仅如此,如前文所述,满语与印尼语在核心词和一系列与爱新觉罗家族起源相关的重要词汇上具有惊人的显著对应关系。而根据大样本新加坡马来人Y染色体数据,新加坡马来人的最高频单倍型与O1a-M119星簇核心型关系密切。
满族与鲁凯族均认为其是蛇的后代,均有十分浓厚的蛇崇拜和鹰崇拜,满语与鲁凯语在一系列重要词汇上具有显著的对应关系。在台湾原住民中,台湾岛南部的三个族群(卑南族、排湾族、鲁凯族)在文化上具有显著与太湖流域先民交流的特征。太湖流域人群的O1a-M119星簇比例高,O1a-M119星簇属于单倍群O1a-M119的下游单倍群——单倍群O1a1a-P203。而在台湾岛南部的三个原住民族群中,鲁凯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和O1a1a-P203比例均为最高(Loo等2011),且是唯一一个最高频单倍型属于单倍群O1a1a-P203的族群(吴芳琴2009)。
这一切,在让人感到惊叹的同时,清晰地显示了爱新觉罗家族与南岛语系民族、与单倍群O1a-M119、与O1a-M119星簇的密切渊源。与根据大样本满族和北京汉族Y染色体数据,符合爱新觉罗家族特征的单倍型均属于O1a-M119星簇是一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Y染色体类型应属于O1a-M119星簇。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