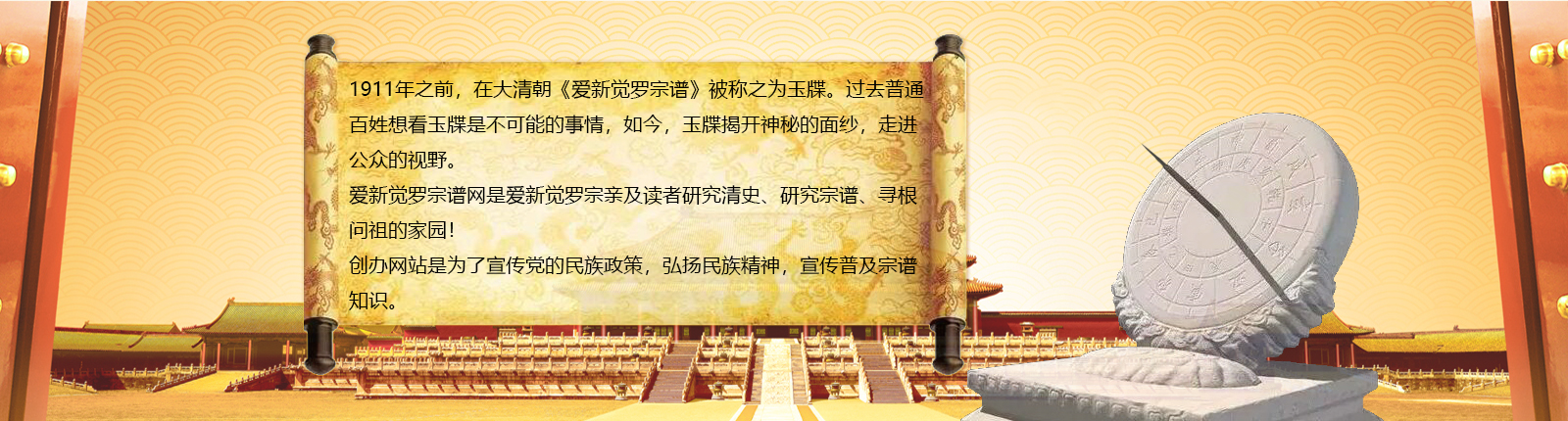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转载于《红缨满洲》,
作者:关嘉禄(满族,瓜尔佳氏;满学满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

满族的崛起,开创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代王朝的宏图大业。回眸16至17世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全过程,从文化层面审视,满族善于学习,富于创造,勇于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追求,赋予了其自身强大的文化推动力,从而一步步发展壮大。而满文的创造则是满族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壮举,洵为满族在崛起进程中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泛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关于文字在文明形成中的地位,早在一百多年前,摩尔根和恩格斯都对此进行了论证。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又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并在该书注中说:“拼音字母之出现,也和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是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迟钝的埃及人改进他们的象形文字,经过若干形式,才形成一个由音符文字构成的方案,而他们所尽的力气也就到此阶段为止。他们能把定型的文字写在石头上了。……腓尼基人创造了由16个符号构成的新奇的字母,及时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书面语言,人类由此有了写作和记载历史的工具。”恩格斯也指出,野蛮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对于文字创造的文化意义,中国史学界公认,文字、城郭、礼器是文明开启的三大标志。汉字的创造和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字“起源于洪荒蒙昧,成形于殷商甲骨,统一于秦小篆,经‘隶变’为汉书、章草、真书、行书迸发,于碑刻上‘从隶到楷’,唐太宗择士取其‘楷法遒美’,于是,中国的字体逐渐定型为‘唐楷’。‘字’,逐渐由一种供奉血缘绵长、预示宗教兴盛的符号,演变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汉语书写系统的统称。先秦儒学、两汉大赋、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官方载录的《二十四史》,无一不是用汉字写就的中华文明史诗”。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审美意识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乎都隐藏在一个个汉字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其古老而又具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中,蕴含着各民族极具智慧的文化创造。其中,少数民族的文字,五彩斑斓,意蕴深厚,承载着每个民族的历史沧桑,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谈到满文,就不能不提到满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是在女真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粘着语类型。作为记录和传达满语的书写符号,扩大满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的文化工具———满文,属于表音文字,更确切地说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从生态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满文的文字类型,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清史馆纂修《国语志》稿本中,卷首有奎善撰〈满文源流〉一文,文中说:“文字所以代结绳,无论何国文字,其纠结屈曲,无不含有结绳遗意。然体制不一,则又以地势而殊。欧洲多水,故英、法国文字横行,如风浪,如水纹。满洲故里多山林,故文字矗立高耸,如古树,如孤峰。盖造文字,本乎人心,人心之灵,实根于天地自然之理,非偶然也。”台湾著名清史满学专家庄吉发先生认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书写,字型矗立高耸,满文的创造,有其文化、地理背景,的确不是偶然的。当然,勿庸讳言,社会因素,对于文字的创造尤为重要。任何一种民族文字的产生,都是该民族所处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满文的创造与当时女真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也赋予其新鲜的内容。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正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率部纵横驰骋,致力于统一女真各部的草创时期。伴随着激烈的军事斗争,建州女真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同明朝、蒙古各部和朝鲜的联系也日益增多,“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国人以为不便”。努尔哈赤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亲自倡议并主持创制满文。这一重大决策,显示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满语,意为旧岗,亦称旧老城,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他说:“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额尔德尼“兼通蒙古、汉文”,“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旨意,招纳降服,赐号‘巴克什’。”据《满文老档》记载:“聪睿恭敬汗所立之一切善政,俱由额尔德尼巴克什录编成书。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参照蒙古字母,结合女真语音义特点,创制了满文。此初创之满文没有圈和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在这里需要说明,女真人曾创制过女真大小两种文字,历经元明,使用范围有限,至努尔哈赤父祖崛起前已基本被弃用,此时的女真人多以蒙古文字作为交际工具。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所参照的蒙古文字,有元音字母5个,辅音字母24个,共计字母29个。多数字母为音节字母,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4种书写形式。一个单词由一个或几个音节字母组成。老满文这种初创文字,字体简古,辨认殊难,字母互相假借,字形亦不统一,正如《满文老档》所说“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显然,老满文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天命朝到天聪朝,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后金国地域不断扩展,汉族聚居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给予满族以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满汉人民接触更加频繁,彼此学习,互相了解,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作为记录满语符号的老满文,在后金社会通行了30余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皇太极天资聪颖,心胸广阔,崇尚文治武功,富于创新精神。顺应时势,他任用达海改进老满文。达海,满洲正蓝旗人,姓觉尔察,“生而颖异”,智慧过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卒于天聪六年(1632年),享年38岁。达海“9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太宗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天聪四年)所译书成,授游击。五年七月赐号‘马克什’。”达海学问淹通,文理精深,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超凡的交际能力,深受皇太极重用。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达海“从征大凌河,既破明兵,擒监学道张春等文武三十三人,达海宣上恩德,谕之使降。十月,复偕石廷柱招降明总兵祖大寿。”次年,达海病重时,“上召侍臣,垂泪谕曰:‘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全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其及身未曾宠任,当优卹其子,尔等以朕言告之。’赐蟒袍,令侍臣齎往。达海闻命,感怆垂泪,已不能言矣。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达海功昭后世,康熙八年(1669年)其孙禅布,时任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赐立碑,得旨:“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令其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勤劳,著仍追立石碑。”在这一谕旨中,康熙帝清晰地指明并肯定了达海改革满文的功绩。经达海改革的满文,后人称之为“加圈点满文”或“新满文”。其改革的着力点,在雍正初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编纂的《八旗通志初集》中作了全面、准确的表述:“太祖初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同噶盖扎尔固齐将蒙古字创立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复命大海(即达海)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又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两字连写切成一字,其用韵之巧较汉字切法更为稳叶。”这里需要说明,新满文在原字母旁酌增圈点,完善并统一了字母形式;增加新字母,后人称为“特定字母”,解决了满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的标记问题;用所谓“切音”,即为两合音为一正字,弥补了满语字母拼写之不足。以上几点,使满文在拼写汉语人名、地名、职官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满汉文化交融更为便利。达海改革老满文,确立新满文,使满文成为一种完善而成熟的文字,是满文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由于满文改革的成功,新兴的满族得以跨进更高文明的门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辽沈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片丰饶的沃土上,满族密切而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孕育并产生了新型的民族文字———满文,这种民族文字反过来又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满文的创制与改革,除社会因素之外,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丰富社会经验、通晓几种民族语言文字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额尔德尼、噶盖、达海等人,在满文的创制及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沧桑,闪烁着独特的文化光芒。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后,面对浩瀚的汉族地区农耕文化的包围,不囿于自身的陈规旧制,采取积极学习的态度,效法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较快地继承并完善了封建社会制度,不但使自身得以立足,而且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反映在语言文字上,满族如饥似渴地吸收并借鉴汉族语言文字的精蕴,把它巧妙地融化在自身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中,从而大大提升了满族的文明程度。
从大量满文历史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伴随着满文的创制和改革,汉语借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满族语言文字中,特别是清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汉语借词愈益丰富。显然,这是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变化的反映,从一个侧面突显了满族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
满文中汉语借词的表现形式
A、直接音译,即把汉语原词的语音和意义原封不动地一并借用。这方面名词类最为丰富。如人名、地名、称谓、衙署名称、职官名称、公文名称、常用名词等。
满族受汉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影响,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满文中大量汉语量词的借用即是明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直接音译。如king顷,mu亩,jang丈,gin斤,fun分,li厘,hao毫,hū斛,giyan间等。(注:满文用罗马字转写,下同)。
某些动词词干直接音译,与满文附加成分及词尾结合一体。如:fungnembi封,diyanlambi典当之典、垫牌之垫,giyangnambi讲,mabulambi用布擦抹等。
B、音译加注,即在直接音译的基础上再附加满文词的注释。如hūng siyoo li šulhe 红肖梨,wenšu bithe文书。这里hūng siyoo li、wenšu为直接音译,šulhe(梨)、bithe(书)为满文注释。
C、半音译半意译,满文中的汉语借词一部分为音译,一部分为意译,两部分合起来为一个借词。如funglu bele禄米,tai i haha台丁,wase boo瓦房,genggiyen cai boo茶房。
D、意译,即吸收汉语词的意义,用满文构词材料和构成方法组成的新词。意译借词在乾隆朝大量出现,这与乾隆帝的大力倡导有直接关系。由于清代社会的发展和乾隆帝本人的重视和干预,由皇帝钦定,对满语文实行大规模地规范,主要是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进一步丰富了满语文的构词手段和词汇,使满语文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乾隆帝曾明确指出:“近见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朕随所见即为改正,复派大臣详查更正。”所谓“清语中杂以汉语”,即指满语文中使用音译汉语借词;“语熟成风”,即是说音译汉语借词使用得十分普遍。在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1700余条。如uheri kadalara amban总督,原音译作dzungdu;giyarime dasara amban巡抚,原音译作siyūn fu。此外,原来音译的汉语量词,在乾隆朝也改为意译借词。如:顷,原作king,后改作delhe;亩,原作mu,后改作imari等等。

从以上所举诸例不难看出,大量汉语借词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满文中,都极大地丰富了满文的词汇,强化了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的功能。除汉语借词外,在满文文献中我们还看到有不少成语、谚语,也借鉴了汉语中的遣词造句规律,增强了满文自身的表现力。古汉文中的诗、词、歌、赋、铭等各种文体,内涵丰富,格律严整,文辞优美。将其翻译成满文时,就要充分借鉴汉语文的格式和韵律,结合满文自身的特点,创造新的修辞方法,从而真正体现汉语文原作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以《全唐文》中刘禹锡所作《陋室铭》前两句为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满文译作:alin den de akū,endurin bici gebungge ombi。Muke šumin de akū,muduri bici ferguwecuke ombi。这里,满文的翻译比照并借鉴了汉文的格律,在字数、结构、对仗、韵律上审慎考究,使其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alin(山)与muke(水)均系名词;den(高)与šumin(深)均系形容词,下接格助词de及无形态变化的动词dkū,对仗十分工整。“有仙则名”和“有龙则灵”句中,bici与ombi组合为合成谓语,不仅意尽言切,对仗严实,而且ombi均放在句尾,以动词词尾mbi形式作为韵脚,读来押韵上口。
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满文作为清朝国书,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受到外国人的青睐。汉文属表意文字,满文是表音文字。对于外国人来说,掌握满文要比学习汉文容易得多。在清代前期,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在康熙帝执政的61年中,前后任用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张诚、巴多明(一译巴道明)、纪理安(一译吉利安、吉里安)、戴进贤、白晋等,为清廷翻译拉丁文文书,这些传教士都通晓汉文、满文,不仅能把满文译成拉丁文,而且也能把拉丁文译成满文。法国人白晋在《康熙帝传略》一书中提到:“他(指康熙)对我们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二十遍。我们把这部书译成了满文,其中包括欧几里德与阿几米德著作中所有重要的定理及其证明。康熙帝还任命法国人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皮里所著的《人体解剖学》。来自意大利的学者尚文博士用史料证明,西学方面的书籍有许多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汉语的,中国的书籍也有不少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西方文字的。以上所举史实,充分说明了满文作为交际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得以交汇贯通,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满文的创造并不断丰富完善,在满族文化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保存至今的浩如烟海的满文文献,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史料保存所望尘莫及,堪称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当今,满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在新世纪新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共享中,满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