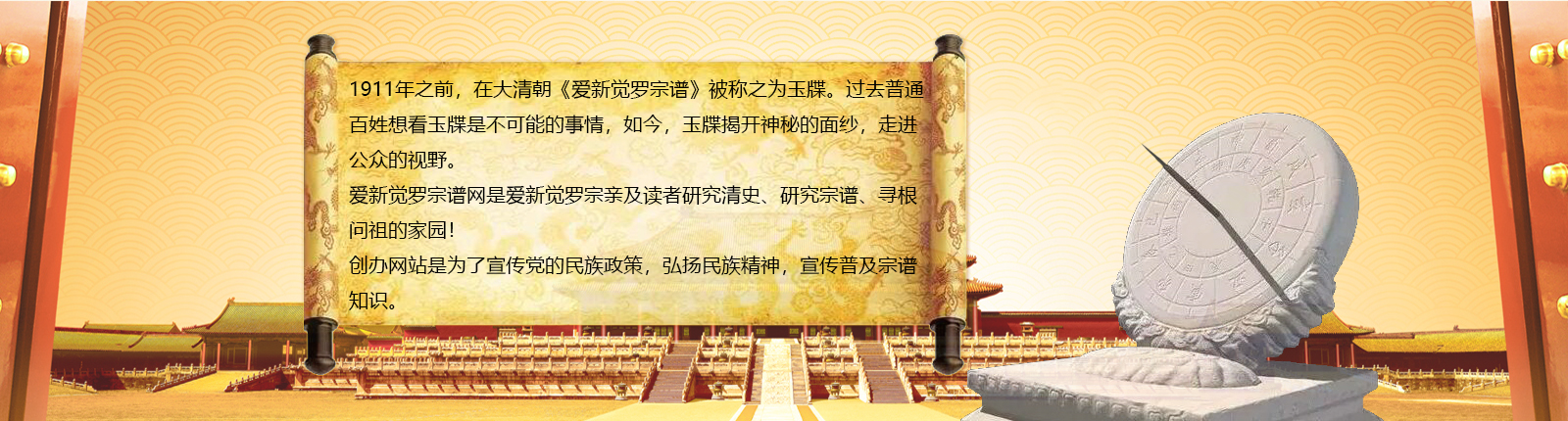


——以内务府“三藩汉女”为中心的考察
刘小萌
清朝有“指婚”一词,指皇室子女婚嫁,由皇帝钦准。与“指婚”不同,本文所用“配婚”一词,特指康熙年间内务府将三藩汉人女子(简称“三藩汉女”),强制配给旗人为妻的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廷平定“三藩之乱”。随即,在清算“罪藩”基础上,对其余部进行大规模清理。一部分罪藩眷属、子弟、亲信、家人,作为抄家籍没对象编入内务府,此即“三藩汉人”之由来。三藩汉人,在清朝官书中写为“ilan fudaraka i nikan”,直译为“三逆汉人”。这种将特定人群冠以“逆”字的做法,足以说明三藩汉人是内务府包衣中身份地位最卑下的一个群体。
关于内务府包衣汉人(nikan,尼堪),学界已有研究。针对盛京官庄,亦发表有不少成果。至于“三藩汉人”,笔者已有初步探考。三藩女子编入内务府后,除丈夫被处死者外,一般随夫分拨;寡妇及未婚少女中的优者(年轻貌美或有才艺者)编入管领,主要在宫中和盛京内务府承担差事或杂役;劣者(年老色衰或无才艺者)则拨入管领下庄屯(皇庄即官庄)。还有一些寡妇、女孩,经皇帝钦准暂时“收揽”(asarambi,存储、收藏之意),以备配婚之需。本文重点利用康熙朝《内务府奏销档》、盛京内务府《黑图档》等满文档案,就“三藩汉女”的配婚 现象作一考察,具体包括配婚汉女的来源、配婚对象的身份、配婚制与满洲领主制的关系、配婚制的终结。以此为切入点,说明康乾时期满洲领主制逐步衰落大背景下,满洲皇室奴仆(包衣)的身份变化。
一、配婚汉女的来源
清廷平定三藩,将罪藩及其亲信处死,与之关系最密切者如眷属、王府包衣、仆妇、侍女、工匠、女乐等,均作为籍没对象,编入内务府。其中的女子来源不一,年龄各异,身份也相当复杂。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从广东出发的尚之信“头队”人口4160人行抵京城。在这批人中,尚之信的眷属(儿媳、侄媳)、家人(包括闲散妇人、寡妇、女孩、蒙古人、朝鲜人等)588人,旧汉人(清入关前归附的辽东汉人)250人,均编入内务府管领。其中,女性709人占85%)。女性占比极高的原因,应与此前清廷将尚之信及弟之节、之璜、之瑛并部属百余人,按谋反律处死有关。他们的遗孀、子女,照例沦为籍没对象。此外,同行的还有“新汉人”3322人,主体为南方汉人(尚藩在南下征战和盘踞东南沿海时期归附的人口)。经鉴别,优者编入管领,劣者编入庄屯。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有原任提督李本深孙媳,伪将军杨宝彦、何秉钧、宋国富、侯德成,伪总兵潘成,伪副将张都林之子张自新夫妇,沈上达儿媳与吴藩、尚藩罪将之眷属、家人共673口押抵京师。其中,女性346口(占51%)。李本深,原贵州提督,后从吴三桂叛。清军克贵阳复降,被杀。沈上达,原尚藩麾下巨商。康熙十九年七月,清廷将之信及其亲信处死,家产籍没。上达被抄家入狱,自缢而亡。至此,李本深、沈上达等人的亲眷、家人等押抵京城,编入内务府。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内务府奏报,陆续送到吴世周之妻孙氏、吴三忠之子老格色夫妇、李记民之妻王氏、郭壮兴12岁女孩高氏;家奴壮丁(booi aha haha)44人、妇女38人、男孩16人、女孩9人。同时送达的还有穆占隐匿的人口142人。共计254口,其中妇女、女孩130人(51%)。按,吴世周为吴三桂一族侄孙辈;郭壮兴为吴三桂婿郭壮图兄弟辈;穆占,满洲将军,率清军进取云南屡建战功,寻因隐占人口被劾。以上254人中,编入庄屯的奴仆152人。其他罪藩、罪将女眷,擅长吹拉弹唱的女子,包括其子女,编入管领。
同月,刑部抄家送到伪御旗官邵亦仁,伪总兵吴云龙、刘直公、吴岳喜之眷属、家奴丁妇男女孩等共计35人,其中女性18人(51%)。将邵亦仁本人及吴云龙等人的女孩编入管领;家奴经鉴别,妇女、女孩各1人交管领,其他人编入庄屯。
同时,兵部、刑部送到吴三桂伪参将陈志宇、伪官傅世窖、尚之信户下(booi)叶福兴等人妻孥、子女、奴仆壮丁(aha haha)等共计403口,其中妇女、女孩约154人(38%)。这些女子中的一部分分拨佐领、管领,一部分与先前编入内务府的家人“合族”(即将一家人安插于同一管领或庄屯)。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兵部、刑部陆续解送伪按察使方梦怀,伪将军付启东、王宏基,伪副将杨红才,吴三桂家妻妾、奴仆等797口到京,其中女性377口(47%)。
同年五月,刑部送到尚之信等属下王子朝等,吴三桂属下孙有明、孙超等,吴世璠家丁(booi haha)吴成朝、郭壮图家丁宋忠泰、太监魏先明隐匿吴三桂家妇王氏,以及园头刘志正之家奴壮丁等共计37人,其中女子17口(46%)。
同月,兵部陆续送到吴藩旧属刘德、李友明、吴兵、周世穗,徐艺云本人及其诸子、妻兄弟,加上先前送到张文喜夫妇,周天禄妻刘氏,程云琨妻张氏、诸子等53人,单独立户奴仆等25人,总计78口,其中女子40人(51%)。分别派往古北口外、山海关等处庄屯,一部分与此前安插当地的族人同住。
以上共8起籍没人口,均由兵、刑等部押解并编入内务府。鉴别后,优者编入管领,劣者拨入庄屯。其中的寡妇、失怙女孩,经内务府拣选,作为配婚对象。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内务府关于“办理抄家人口”的一件奏报称:尚之信妾陈氏、张氏、李氏,魏普妻吴氏,侍卫郭襄妾杨氏,吴三桂家持锁钥妇人(女管家)等共11人遵旨“收揽”;同时“收揽”的还有女孩、女乐65名。又,户部取来单身妇女、女孩109名,平均分给20个管领,作为“管领下单身”“穷庄头、园头”之妻。当时,内务府管领共有20个,相当于每管领各分配5到6人。另有26名妇女,俱系“次等”,分配给吉林打牲乌拉无妻额丁。此次共分配三藩汉女211人,其中“收揽”以备配婚之用者76人。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内务府奏销档》中,这是记载配婚人数最多的一起。
二、配婚对象的身份
作为三藩汉女配婚对象的内务府旗人,主要有二类,一类为包衣上三旗侍卫与旗员,再一类为包衣上三旗佐领、管领下穷兵、穷丁。关于前类人员,笔者另文已述,不再重复。这里,仅就第二类人员的身份、配婚原因略作说明。这类人员是配婚的主要对象,身份包括柏唐阿、兵丁、牧丁、辛者库人、庄丁,配婚原因均与家境贫寒有关,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因贫无力娶妻。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内务府具奏:正白旗包衣桑格佐领下牧丁洪泰,因家贫,二十三岁尚未娶妻,请求将尚之信家寡妇高氏赏给为妻;正黄旗花色佐领下牧丁毛金生,三十岁,无力娶妻,请求将尚之信原任包衣达(管领)方玉直之妾赐给为妻。他们的请求,均由内务府奏准实行。
第二种情况,妻殁无力续聘。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总管内务府具奏,孝陵掌关防郎中狗塞等呈称:看守中卫营索礼佐领下尼喀达、花色佐领下常明2人诉称妻子俱亡,今无力娶妻,家中亦无阿哈(奴仆),请将籍没妇女赐给为妻。经内务府奏准,将刑部送到吴三桂家寡妇胡氏赐予常明,吴传弼家寡妇某氏赐予尼喀达。孝陵位于清东陵,是清世祖福临、孝献皇后董鄂氏、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陵寝。尼喀达、常明是看守陵寝穷旗人,既无财力娶妻,又无奴仆驱使。又如,正白旗浑带管领下骁骑校阿赖陈请称:欲娶妻而家甚贫,大人若怜,请将籍没尚之信家寡妇陈氏赏给为妻。内务府总管将其陈诉转奏,奉旨:“著赐之(bu),钦此。”镶黄旗僧格管领下骆驼群牧人宜锡,妻子本年病故,自己留在牧群,无力娶妻,请求将籍没吴三桂家使女花儿赐给为妻。其陈诉经逐级转奏,经皇帝钦准。又,正黄旗包衣多弼佐领下护军那颜色,妻殁家贫,无力续娶,请求将吴应贞家女孩大姐,二十六岁,赐给为妻。正白旗马尔汉管领狗上护军校桑格妻殁,无力续娶,请将吴三桂家妇人苏姐赐为妻。海章管领下游牧地羊马十队首领杨世茂丧妻年余,无力娶妻,请求将吴三桂家妇人六姐赐给。汪颜管领下护军肖永芳妻殁二年,无力续娶,请将吴努春由云南撤兵携来妇人吴姐赐为妻。正白旗包衣佐领下牧丁马云腾妻殁三年,无力续娶,请将籍没吴世璠家寡妇耿氏赐为妻。
以上呈请赐妻者10例,核检《八旗通志初集》卷二至五《旗分志》,可以认定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佐领和管领下人。其中,家贫无力娶妻4例,妻亡无力续娶6例。申请配妻者中,身份不明者2例,护军、护军校3例,骁骑校1例,牧丁(包括牧丁首领)4例。牧丁为数最多, 凸显了其生活的艰窘。而作为其指配对象的,则是已处死罪藩、罪将、罪官的妻妾、儿媳、管家、女仆,以及未成年女孩。其中,尚之信家人3,吴三桂属人7。按,吴应贞,应系吴三桂子侄辈。吴世璠,吴三桂孙,清廷额驸吴应熊嫡长子,吴周第二任皇帝,前已自杀。一牧丁请娶吴世璠家寡妇耿氏,此耿氏是否耿精忠一族无从确认。吴努春由云南撤兵携回之妇人,应为吴三桂旧属。对于内务府的奏陈,康熙帝朱批用的是同一个满语词“给”(bumbi)的命令式:“bu”,可译为“著给之”。因皇帝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可译为“著赐之”。在这种场合,皇帝朱批反映的完全是同一种程式。此类配婚女子,均由提出申请的穷兵、穷丁直接点名。这与皇帝赐婚内三旗侍卫或旗员,先由内务府提名,复经皇帝钦准的程序有所不同。究其原因,这些女子作为籍没人口,此前应已分配给内务府各佐领管领,故申请者对她们的情况并不陌生。实际上,无论选取程序有无异同,最终决定弃取的,既非婚配双方,亦非内务府总管,而是作为内务府包衣最高领主的满洲皇帝。
三、配婚制与满洲领主制的关系
将三藩汉女配给内务府包衣的做法始见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强制性的配婚在满洲社会中却源远流长。天聪年间定,贝勒私属女子出嫁,须经部转呈各王、贝勒、贝子后方许适人,私自予人者有罪。说明作为满洲亲贵私属的女子,出嫁必须经由领主同意,否则治罪。清朝入关后,内务府包衣的领主是满洲皇帝。包衣的身份虽有分化,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并未削弱。顺治四年(1647)七月皇帝谕旨:将苏拜的少女配给恭阿尔之子,命看守苏拜之墓。同年,内务府总管致书盛京包衣佐领:看守某庄头地窖之包衣,有十五岁女孩,一只眼瞎,命配与苏和钦。又命索尔格之女配给达因布鲁珠轩(juhiyan,又作朱显)的费亚汗为妻;珠轩头目岱因达哈之妹,配给奥尔陶珠轩的肯特为妻;岱因达哈珠轩的洪古托之女,配给额齐布珠轩的伦拜为妻。珠轩是内务府设在盛京、吉林打牲乌拉等处打鱼、捕水獭、采珠、采蜜的组织。这三名女孩及配偶,都是当地的珠轩户。他们居处边外,距京城遥远,但在择偶问题上,仍须服从内务府指配,并经皇帝“钦准”。
同时,严禁包衣女孩外嫁。顺治五年二月,内务府命盛京包衣两佐领下的女孩和棉、靛庄(拖克索)女孩,视父母同意,于两佐领和棉、靛庄内出聘;盛京若无相配之人,可于北京汉人八佐领出聘。若聘予外旗(tulergi gūsa),罪之。又命,十粮庄女孩亦于庄内酌情出聘,若私自聘予旗外之人(gūwa tulergi niyalma),罪之。笔者按,当时盛京地区,共有内府佐领2,粮庄10,盐庄5,棉靛庄若干;“汉人八佐领”,应指包衣上三旗的8个汉军佐领(又称旗鼓佐领)。内务府发出此命之目的,显然是严格限定盛京包衣女孩的聘娶范围,一般限制在包衣两佐领和官庄内。在本地没有合适配偶的情况下,也可远嫁京城内务府旗鼓佐领下人。同时,禁止嫁给“外旗”或“旗外之人”。此处的“旗”,应指外八旗。
对私自出嫁的包衣女子,抽回后强制配婚。顺治十八年奏准,“凡佐领、管领下女子、寡妇,倘违禁不报佐领、内管领、领催等,私将其嫁给旗民,则将女子父母及娶者一并治罪,并将已嫁之女子、寡妇抽回充为内奴”。盛京鄂博佐领下棉庄庄头朝鲜人明吉里,将妹私嫁给官庄之人,多年后案发。明吉里等被解送盛京刑部审理,并强行将私嫁之女与其夫分开,配给管领下无妻庄丁。此案表明,即使是官庄内部通婚,一旦发现是私自出嫁,该管官员、庄头、女方父母及聘娶者一并治罪。
对亡丁之妻、逃丁之妻,强制配婚。顺治十六年,官庄额丁色科亡。包衣佐领安塔木将其遗孀配给另一管领下庄头高某之弟。顺治十八年颁布谕旨:“逃丁满一年者将其妻配夫,嗣后永为定例。”康熙四年,盛京法喀管领、杜楞额管领下壮丁陈大等四人逃亡已至六载,包衣佐领据上引旧例,将四人之妻配给庄中无妻之丁。
清制,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必须选验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康熙八年,总管内务府咨文盛京包衣佐领辛达里称:选验(选秀女)之后,各庄、园、牲丁等所属女子,倘不于各所在人中婚嫁,私行嫁给旗民人等,当照前定之例,除将所嫁之女抽回,并将嫁娶双方治罪外,即令庄内女子于庄内婚嫁,园内女子于园内婚嫁,打牲人之女子于打牲人内婚嫁。倘私行婚嫁,则将许配之人鞭八十,罢其原差充为下人,聘娶之人亦鞭八十。下属额丁知而不举,每人鞭五十。与顺治五年旧例比,此禁令更为严厉,一是划定婚嫁范围更窄,只准于所在庄、园、打牲地缔结;二是对私嫁双方,在既有惩罚之上,又增加鞭刑。此后60年间,该禁令一直有效,即强制私嫁女与丈夫离婚,配给管领下“无妻末等庸懦之人”。迄至康熙四十七年始改为:女子私嫁庄头或庄内额丁,停止分开,将嫁娶及隐匿者交佐领各鞭一百。所以有此改动,显然是考虑到将已婚夫妇强行拆散并另配他人,与已为满人社会逐渐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明显相悖。自此,惩罚力度明显减轻。
康熙朝平定三藩,将三藩汉女编入内务府,强制配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三藩汉女与配婚对象虽都是包衣,但他(她)们的实际地位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此前,包衣女子在婚配范围和婚配对象上虽受到严格限制,但只要不违背禁令,在狭小范围内仍有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余地。与之不同,三藩汉女的“配婚”,则完全无视女方意愿,不仅充分体现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专横,同时表明,作为“叛逆”家属或仆妇而被籍没的三藩汉女,显然处于内府包衣这一等级结构的最下层。
三、配妻制的终结
康熙后期,内务府为解决穷丁娶妻,开始了从配妻制到赏银制的转型。
清朝入关初,在内务府佐领、管领中,已有给穷丁赏银买妻的做法。顺治十三年统计,盛京各庄有无妻额丁78名。内官监(顺治十年设,十七年改宣徽院,康熙十六年改会计司)以其“承担耕耘之苦、复有孤身一人之累,不可不给妻”为由,札饬盛京包衣佐领安塔木,动支官庄卖粮银买妇配给之。康熙九年,盛京24庄头诉称,无力娶妻之丁每庄8名以下、2名以上,呈请“照先例买妇配给之”。惟盛京各庄陈粮无多,换银有限,且山海关内外各庄新丁中无妻者亦多,故所议不准行。
清廷平定三藩后,将籍没女子编入内务府,其中除从夫分拨者外,寡妇、失怙少女就成为配给穷丁的重要来源。但此类女子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众多无妻穷丁的需求。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盛京包衣佐领福贵向内务府会计司咨称:20个管领内,因贫无力娶妻人52名,包括捕水獭丁、蜜丁、砍箭杆丁、披甲(打牲甲丁)、牧丁、扫院丁、铁匠、熟皮匠、仓书等;3包衣佐领内无力娶妻人43名,职业多为织布(毛青布)匠、染匠等,因本处没有适合配婚女子,呈请京城内务府从籍没人口中配给。对于福贵给95名穷丁配妻的请求,会计司答复称:查看定例,“佐领管领内若有寡妇、失怙女孩(anaha sargan juse), 佐领者则在佐领,管领者则在管领,俱各依父母,自愿嫁娶”。并明确答复说,本处佐领管领下无妻人已全部查看,将籍没妇人、女孩赐予为妻之事碍难实行。会计司还斥责福贵“将无成例之事,并不详察,借投诉之名卖人情于下属(habšaha be tuwame fejergi urse de dere gaime)”。如前所述,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内务府曾将单身妇女、女孩109名平均分给20个管领,作为管领下单身、穷庄头、园头之妻;同时,将次等妇人26口,配给打牲乌拉无妻额丁。但对于盛京穷丁来说,却没有普沾“皇恩”。
由于穷丁配妻问题久拖未决,盛京包衣佐领只好多次向内务府呈文反映。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福贵呈报,众管领下无妻柏唐阿41,苏拉11,共计52。因盛京地方管领下人少,此等穷人有到三四十岁仍未娶妻者,且41名无妻柏唐阿内,属于独子的有14人。他强调说,这些人中,最困难的当属“因贫”用为牧丁或放犬捉牲的柏唐阿,请求优先配妻。二十四年九月,针对盛京佐领三官保再次呈请,会计司回复称:“此二年陆续送来寡妇、女孩内,有一二好者已具奏编入管领,次等者编入庄屯。被抄家产内之寡妇、女孩,今既办理完毕,将福贵等呈报记录在案,俟日后收到抄家籍没寡妇、女孩时再议”。所谓“办理完毕”,是说三藩汉女分配已尽,没有剩余;所称“待议”,是明确告知对方,俟日后获得籍没女子时再议。在这种背景下,盛京包衣佐领不得不呈请恢复内务府赏银买妻配给穷丁的旧例。
京城内务府既统摄包衣事务,为何在配给盛京穷丁妻子一事上却态度消极?究其原因,大致有三:1、用于配婚的三藩汉女人数较少,不能充分满足各地穷丁的需求。2、盛京官庄的主体是三藩汉人,他们在内务府各色包衣中,编入最晚,身份最低。诚如学者所云:在京城和盛京包衣佐领、管领下的庄丁、柏唐阿、辛者库人,实际待遇有别,不能混为一谈。3、与内务府管理体制有关,即京畿等处事务一向由内务府各衙门直接负责,而盛京事务则直属盛京包衣佐领。因隶属关系的差异,会计司一向倾向优先处理本辖区事务。其实,不仅在穷丁配妻问题上,包括补给官庄丁妇、官牛额缺诸事,京城内务府对盛京佐领的请求同样态度消极。康熙二十五年,包衣佐领三官保在给内务府呈文中抱怨说:“所给人丁,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之二三人不抵一人之劳作。此项逃跑、死亡者之缺,乞请补给人丁,曾两次诉告,业已转行京城去讫。后准咨复称,俟有人时再予补给,唯至今未得其人。”新编官庄的丁妇,均系三藩汉人。因陆续逃跑、死亡,56庄共缺丁194名、妇34口。京城内务府虽答应视缺额情况陆续补给,却未曾落实。康熙四十四年,众庄头再次呈报:“康熙二十二年将身等编庄后,每庄各给十五对人。因所给之丁、妇皆为南方汉人,死的死,逃的逃,现有六七丁之庄或八九丁之庄居多,丁、妇各十五名之庄极少。为缺少丁、妇曾经声诉,然至今并无补给之处。”尽管盛京包衣佐领反复呈请,此后多年,内务府仍“未曾补给一丁一妇”。
穷丁娶妻难问题,除了穷丁生计艰窘外,又加上丁妇不断逃、亡,造成各庄内部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久延不决,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此等单身额丁若无妻,不能生养”,势必影响官庄人口的再生产,使官庄生产难以为继;二是造成庄丁情绪低落,并助长逃跑之风,“此等人役,因无室家(家室),往往不务生计,逃避官差”, 同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在这些压力下,吉林、盛京等地开始尝试新的措施。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呈报,本处有12丁之妻亡故、15丁无妻、14丁已另行说亲。“定例载:妻亡与无妻之丁,应给女人。另行说亲之丁,每人应发给毛青布10、棉花十斤”。所谓“另行说亲之丁”,顾名思义,应指通过“媒妁之言”自行订亲的牲丁。穆克登呈请依照此例,配给无妻之27丁女人各一,令会计司配给;另行说亲14丁,每人毛青布10匹、棉花10斤,令广储司发给。上引定例初次颁布时间不详,估计在康熙中叶,也就是三藩汉女来源枯竭之际。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依等呈请,本处有无妻牲丁、蜜丁7人,另行说亲牲丁10人,仍照旧例办理。
上述事实说明,在籍没女子减少的情况下,约自康熙中叶起,打牲乌拉等地对无妻穷丁开始兼用两种方式,一是对一部分穷丁,依旧由会计司配给籍没女;二是对一部分愿意自行择妻的牲丁,由广储司负责,给与一定物质鼓励(毛青布、棉花)。鼓励自行提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减轻内务府给穷丁配妻的压力。申请自行提亲的穷丁增多,反映了内务府对包衣聘娶限制的松弛。同时,这一现象也与内地汉民的流入有一定关系。流民的进入,为穷丁娶妻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因此才有“另行说亲”的可能。
类似变化亦见于盛京地区。康熙四十二年十月,盛京礼部侍郎哈山疏请发出盛京户部银4万两,仿照公库例,1分生息,以六年为期,本还户部,可得息银28000余两,陆续给与160余无妻穷丁“完娶银”,每人50两银。下部议,从之。这种经皇帝钦准,由内务府负责,借取内帑库银生息,然后把“滋生”子息(息银、余利银)赏给八旗内务府穷丁的做法,称“生息银两”制度。盛京是试行“生息银两”制度的地区。早在康熙初期,盛京包衣佐领已有用“内帑银两”交商人营运,坐收利息之事。康熙三十二年,在东北驿站亦有用库银生息赏给站丁娶妻的事例。从更大范围讲,这也是清廷推行“生息银两”制度(恩赏银制度),用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措施之一。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盛京所属粮庄88个,共有丁1533人,其内无妻额丁440人。包衣佐领特巴库呈请,仍照从前“借取库银,贷放生息,买妇娶妻例”,发出盛京内库存银5万两,每两取息5厘,借给殷实富裕之户,所得息银赏给单身额丁买妇。盛京官庄(粮庄)无妻额丁440人,占到总额的34%。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穷丁娶妻难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呈加剧趋势。特巴库的建议与打牲乌拉对无妻穷丁赏给生活用品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真正落实的难度也相当大。正如档案所透露的,购买一妇的价格高达50两,说明人口市场的供给并不充足。动用5万两库银,按每两5厘取息(即5% 利息),在较短时间内能否筹得2万余两息银(每丁50两,440丁约需22000两)也是问题。此项建议是否得以顺利实施,因档案缺载,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变化还是比较清晰的,即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包衣穷丁的配婚制迅速为恩赏银制度所取代。
满洲统治者给穷兵穷丁配婚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包衣人口的繁殖,维持内务府各机构的正常运转,避免皇室利益遭受损失。但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使女子“入官为奴”的来源近乎枯竭。在此背景下,满洲统治者只有改弦易辙,尝试用库银取息、鼓励择亲等方式解决问题。与强制配婚相比,后者是一种较为柔性的经济手段。但穷丁无力娶妻现象的蔓延,归根结底还是满洲领主制的困厄。制度问题不解决,领主对包衣的人身控制依旧,领主经济的内部矛盾根深蒂固,注定穷丁贫困化所衍生的娶妻难问题无从化解。
乾隆初,以内务府官庄为代表的满洲领主制经济日趋瓦解为背景,对包衣女子的聘娶限制大为松弛。乾隆二年(1737)四月,帝谕八旗内务府:“向来包衣管领下女子,不准聘与包衣佐领下人;包衣佐领下女子,不准聘与八旗之人。......八旗暨包衣佐领下人等,俱朕之臣庶,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以此为契机,横亘在八旗社会内部,包衣佐领下人与管领下人之间、庄头与庄丁之间、内府包衣与外八旗人之间的婚姻障碍不复存在。不久,又谕:“及时完婚,乃王政所重,理应体恤怨女旷夫。”并宣布:对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佐领下兵丁闲散,凡28岁以上男女,因家贫无力聘娶者,每人赏银15两;对内务府包衣佐领下额丁,赏银减半(实际各给7两),以完婚事。“恩赏银”虽有等差之别,对偏远地区的包衣穷丁说来亦属雨露均沾,不遗荒陬。内务府复对京畿、山海关内外、锦州、热河、盛京、宁古塔等处包衣旷夫怨女作了全面调查,并就赏银的领取、管理、监督、发放、核查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乾隆三年七月至五年十月,盛京包衣佐领分5次从内务府广储司领取份银1204两,分别赏给粮庄所属“因家贫无力聘娶”之丁169人、未出嫁之女3人。从领赏名单可以得知,大多数穷丁的年龄都在三十四、五岁上下,最高的达到五十三、四岁。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按康熙五十二年每丁赏银50两买妻旧例办理,169丁共需银8450两,此次却减为每丁赏给7两(相当于原额的七分之一)。如何理解其中的变化?笔者认为,除了内务府减少恩赏银支出的现实考虑外,关键一点还在于关外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即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民流入盛京地区,不仅买妻(或聘妻)的费用大幅减少,穷丁娶妻也有了更多选择。这应是内务府公文关于恩赏银的措辞从当初的“买妇娶妻”改为“娶妻领银”“商议结亲”或“各自结亲”的主要原因。同时,随着颁给恩赏银成为内三旗包衣与外八旗人共享的一项福利措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务府包衣身份的提高。
乾隆十年,内务府官庄将庄丁大规模放出为民。不久,内务府和下五旗府属佐领非满洲血统包衣,包括北京蒙古分给之汉人、辛者库汉人、旧汉人、旗鼓佐领汉人、别载册籍汉人、匠役汉人、校尉汉人、投充汉人、抚顺汉人等,相继出旗为民。内务府和下五旗包衣大批出旗为民,标志着满洲领主制的衰落以及向租佃制经济的转型。随着内务府主奴关系的嬗变,对包衣女子的强制配婚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转载自《清史研究》)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